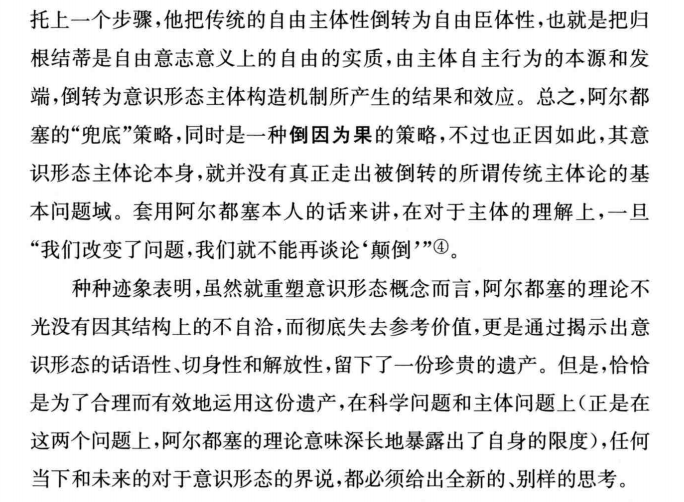如何评价路易·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
- 431 个点赞 👍
目田导师、哲学界何同学、政治丁真这样评价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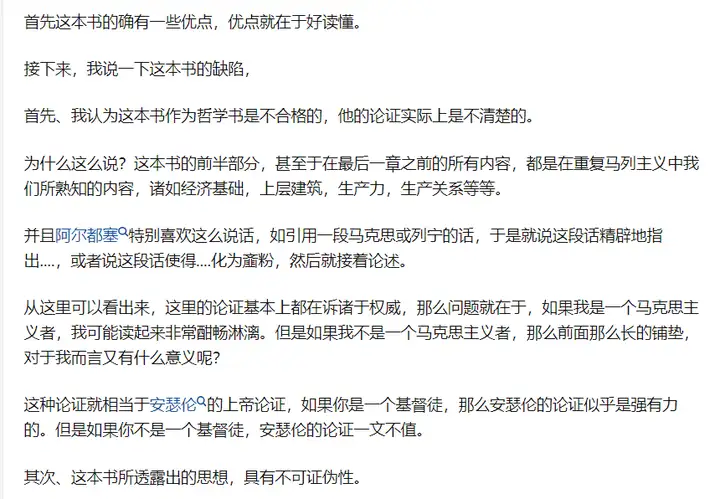
毫无疑问这只是洗粉用的现代工业的馋赤品,回答者本身并不在乎对面是阿尔都塞还是阿尔冯斯、阿方索、阿里巴巴,《论再生产》也并不是用作打靶的标的物,随便替换成任何一本马列主义的典籍都可以,因为回答者推崇的此类所谓学术著作是类似《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分野》等南巡时代催生的古墓派。回答者自己就是意识形态机器学说的最佳注脚,其所批评的什么哲学不合格、论证不清楚、重复、诉诸权威、“如果不是一个目田儒棍那看这些有什么意义”、不可证伪,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回旋镖,扎的都是它自己罢了。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子。一直以来,这种无穷的追问、眼中有刺而看不见梁木都笼罩着正统学界的主流看法,区别无非是用学术范式撰稿,拽一些文词;这样的质疑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中也有值得思考之处——突出的例子便是构境者兵兵。
对《论再生产》和阿尔都塞困境的书写早有人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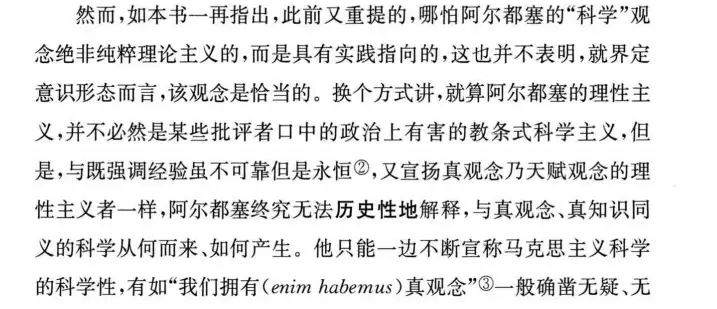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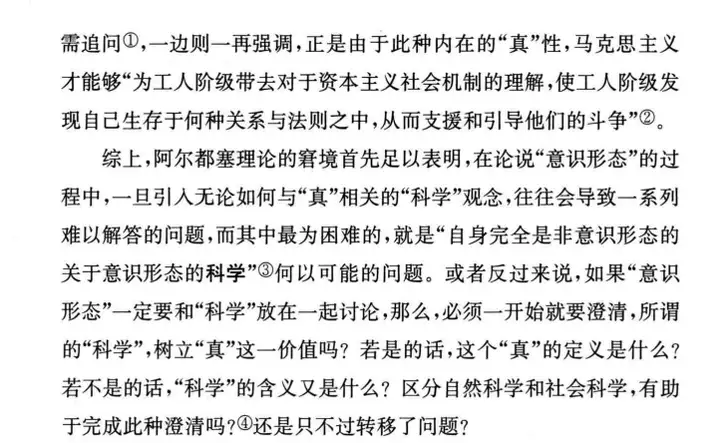
“如果不是工人阶级、不信奉弥赛亚的马主义,那么这样的学说岂不是毫无价值?”“为什么这就是科学的,这就是真?”
作者王春明认为,这种无法解释的缺陷是由于阿尔都塞的主体性内生的框架造成的,阿尔都塞对传统主体性的解构没有超越传统,以至于本身必须完全依附主体性观念展开,否则就会直接瓦解。
作者认为,阿尔都塞理论指出的马主义是加工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意识形态,在保留意识形态结构的同时,去中心化、去镜像化;但是这种单纯的逆反式断言并不能对主体性内涵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说明。
当然,这种批判与质疑能否真的直达阿尔都塞理论核心,仍然是未知的。至少有两个阿尔都塞在法国的精神废墟上行走:一个来自《黑母牛》,一个来自偶然相遇主义的天主教徒……
虽然最后的人生充满争议性与精神病人的标签,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停止意识的再生产:
哲学的内在要求就是把许多不同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但这就意味着它要处理大规模的阶级冲突以及历史的大事件,它要怎么做呢?它产生了一种范畴装置,把这些相异的社会实践置于它们的意识形态之下。哲学产生了一般性的哲学问题,通过这种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它就可以思考和解决所有的问题。最终哲学产生了许多的理论图景和理论形象,并以此超越了所有矛盾,把意识形态中相异的片段连结起来。此外,它还要通过理性的言说来保卫这一秩序的真理。
如今的统治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虚假的人权意识形态,甚至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律意识形态,而是自1850年起,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逻辑论与数学化的新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再加上一些生物主义、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调味料。从这一点来看,如今苏联和美国的实际的统治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是非常相似的。
在当今的意识形态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正确有效的哲学战略结合起来,寻找一种能让社会前进的新的意识形态。(1988)丧失霸权和统治权的时代,哲人王也许重要,但是无疑马基雅维利们是更重要的。
发布于 2022-10-31 22:57・IP 属地湖北查看全文>>
合田一人 - 212 个点赞 👍
本来刚吃完饭回来身体就不怎么舒服,看到 的回答,脑瓜真是一下子嗡嗡的。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行不行。诚然,怎么评价是你的自由,但你对《论再生产》的整个文本以及对阿尔都塞哲学思想一窍不通,甚至是胡扯一气,我真是有点忍不了了。
先来看 的第一个质疑点,所谓的“引用马克思和列宁过多,诉诸权威”。啊?你是不是对阿尔都塞的理论努力和研究方向一无所知啊。早在1955年《历史哲学的难题》中,阿尔都塞通过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黑格尔等人历史哲学的对比,就已经阐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开辟出一条历史科学的道路。而《读资本论》时期,阿尔都塞在批判经验论与唯心论的共同前提(认识与现实相符合)以及实践的平均主义(把理论实践与现实实践混为一谈)后,明确指出了如何以科学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究竟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
赋予马克思所产生的认识以认识根据的不是以后的历史实践。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所产生的认识的‘真理’标准是由它的理论实践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是由它的可检验性提供的,由保证这些认识产生的形式的科学性提供的。
在阿尔都塞看来,理论的发展必须依靠理论实践本身,而任何现实的经验,都必须首先被转化为由理论所加工的概念对象的形式(也就是说,预先被问题式加工),才能对理论实践起干预作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经济学家不是直接面对市场,而是唯有在其理论架座中才能处理市场;物理学在解决力的问题之前,必须把对象预先处理为力,而不是上帝意志(世俗神学)。
因此,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援引,完全服从于其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理论实践;并且,阿尔都塞通过对现实实践的理论化处置,发展了他所援引的几乎一切命题。我倒想问问,如果阿尔都塞不先援引马列的原文,你又怎么知道他的理论实践发展了什么呢?只有把《论再生产》纳入理论实践的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而且《论再生产》本身就是这一脉络的产物。你 在这发什么颠呢?还“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能读起来很爽,但如果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都不知道你是长了什么脑回路能说出这种蠢话。你为什么不去问问数学家:“你用了那么多符号,搞了那么多证明,如果我了解你的学术方向,我可能读起来很爽;但我不是一个数学家,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愚蠢的话术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门学科上,就连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本身也是延着自身的范式发展的;而站在学科实践的外部,总是可以问出同样的屁话。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倒建议你不如先问问自己,你又是个()()呢?
其次, 你到底知不知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啊?居然能说出什么“如果我不承认资产阶级具有意识形态,那么我能说服阿尔都塞吗?”这就是纯属不知道“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要做什么,才能说出的蠢话。《论再生产》以前,阿尔都塞是以两种方式处理意识形态的,《保马》里把意识形态处理成了一个先于意识的表象体系,对于现实的意识是以此种表象体系为前提;《读资本论》中,意识形态则与问题式相关联,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会把同一对象纳入到不同的问题式进行分析。《论再生产》则是对两个命题的综合,在此,意识形态是中性的并且是永恒的,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不过是人组织自身意识的方式、是人体会自身与现实关系的一定方式;而不同阶级则以不同方式体组织意识、体会现实。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杀人有罪”,如果这一命题为人所接受,那么它就构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而对“专制是否适宜”这一命题,封建统治者与资产阶级也没能达成一致——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看待该问题的。如果林先生连这也要质疑,那么他的脑子要么是停留于无意识的乱流,要么是只发展出了单纯的感性确定性。
我们再来看看林先生津津乐道的“不可证伪”,看看林先生在这里又有哪些可笑之处,我们暂且不谈波普尔的这个命题能不能界定科学,也不谈是否某物不可证伪就失去了真理性,更不谈阿尔都塞对于理论实践的阐述与波普尔完全不一致。你林先生用个“不可证伪”就去反驳阿尔都塞,本身不就证明你处于另一种问题式-意识形态中吗?更不用说,不可证伪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本身就是伪命题。十月革命的成功证伪了先进国家率先革命这一论断、斯大林体制的危害证伪了“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人阿尔都塞把现实实践转变为理论生产的对象,不断改写着马克思的命题,甚至后期直接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拆解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一般架构,到你这成了不可证伪。那你倒说说有几门社会学科是可以证伪的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你要是没先狠狠地攻击一万遍自然法学派,就跑过来攻击阿尔都塞,我觉得你多少是有点不乖了。人阿尔都塞自己也说了,他给出的镜像结构只是一种解释框架,目的是填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它是一种架构,近似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均衡模型,就算不能证伪,它就是假的/无意义的了?什么捉急的逻辑。
还有,我严重怀疑你脑子是不是真被蜥蜴人占领了,正常人能整出个蜥蜴人论证的大活?来, ,你告诉我,你读《论再生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阿尔都塞批判了两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其中一种就是把意识形态理解成“专制者、僧侣(蜥蜴人同理)的欺骗”?我再说一遍,意识形态是人与其现实的想象性关系,这一关系必然是想象性质的,因为人不可能无中介的直面现实。如果没有一个大他者(意识形态)做担保,任何命题都不可能成立。拐卖儿童是邪恶的,但在拐卖儿童和邪恶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的关系,它既不是综合也不是分析更不是先天综合命题,它只是由实践所建构出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目田喜欢的《1984》其实理论水平很低,因为他和林先生一样,在欺骗和现实之间做了愚蠢的二元切割,并且把意识形态归于欺骗一端;于是只要克服了欺骗就获得了无意识形态的现实;而事实则是,人所把握的现实本身就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你书都没读明白呢,就隔这蜥蜴人长蜥蜴人短的,我看你自己就最像蜥蜴人。
另外,林先生说什么“资产阶级出版机构出版法共文献,是否说明这些书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有什么“资本主义无政府生产,为什么会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纯粹的不学无术,胡搅蛮缠,而且充分暴露出林先生对《论再生产》到底在说什么是完全无知的。来,我告诉你,生产关系的统一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来不是对立的范畴;不如说正相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你是无政府生产,但是价格调节、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几乎发生在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是统一,而这种统一性就保证了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可能。另外,你林先生所谓的“统一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除了在第八章还是第几章提了几嘴以外,其他情况下都是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处理为充满断裂与矛盾的集合体,他区分出八种意识形态装置,是因为每一种装置中都配备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绝不是无摩擦的、甚至是彼此尖锐对立的。他们的统一之处不过在于,都支持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运转/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此外,利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斗争,本身就是阿尔都塞讨论的重点之一。而此种斗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任何国家机器在实现初级意识形态的同时,都必然再生产出次级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次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关于初级意识形态与次级意识形态的相互纠缠,阿尔都塞用巴黎公社、用《资本论》的出版、用法共的议会斗争,做了历史与实践的考察。你问出阿尔都塞已经解答过的问题,除了说明你对阿尔都塞的理解过于肤浅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林先生大概也知道自己是纯纯在这胡扯,于是不得不再次吹响cr的狗哨。然而诉诸于所谓的“众所周知”,不过意味着你林先生既不想也没能力去对cr展开分析。阿尔都塞从来没有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只能以cr的方式搞,相反,阿尔都塞在《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明确谈论了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展开斗争的必要与可能;先锋队理论,阿尔都塞也做了一定修改;而且,把cr理解成极权,这就纯粹是目田用自己浅薄的自由-极权二元范式制造出的理论产物了。你再这么鬼扯,我就不得不谈谈自由主义与极权之间到底是怎样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了。
对阿尔都塞的最终评价是,“洋洋洒洒四百字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具有意识形态性”,那不是阿尔都塞的问题,那是因为以你的水平,你也就能理解到这种程度了。我建议你赶紧去研究蜥蜴人,别搁这糟蹋人阿尔都塞的著作了。什么文字简白观点粗糙,什么哲学论证不清楚,我寻思你读都没读明白的人,也能这么大言不惭地评价人写的书?野猪吃不了细糠了属于是。
发布于 2022-10-29 03:08・IP 属地北京查看全文>>
zzx - 64 个点赞 👍
阿尔都塞一生主要干两件事,第一件是怼西马,怼新的黑格尔派,维护列斯权威。第二件事,是学习马基雅维利,祈求罗慕路斯版哲人王,即罗马版的李世民大帝。
这两个其实都离不开葛兰西,比较完整继承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是普兰查斯以及拉克劳等。
这一派的方法就是将葛兰西的阵地战,领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新的概念“链接”和"机器”,链接指的是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就像是铁锁连环一样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结构就像是这些交缠在一起的锁链。要解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就得将其解锁,然后重新链接。因为劳动分工导致不同领域专业化,细分化,序列化,导致每个劳动者都在自己的细分领域中,无法从总体上识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某种单独的观念或是这些观念的简单集合,而是通过在不同知识生产领域中的组合排列,从而将自己巧妙地伪装在各种技术知识的组织关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所有人。更进一步说,我们看到的所有主体哲学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虚假的构象,是不自觉地为“大他者”服务。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整个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基础的构型。
机器指的是意识形态生产就像流水线一样,占据领导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会不断复制生产的整个过程,不断把客观的知识以及感觉材料整合加工成新的意识形态,然后不断自我复制生产。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几句话就能说清。用不着什么玄学词汇。
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很大问题,要不后期也不会转向祈求罗慕路斯大帝的降临,转向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般的决断论。
因为结构主义无法解释一个社会阶段是怎么进入另一个社会阶段,一个历史结构是怎么进入下一个历史结构的。他只能看到这些结构的不断自我复制和生产,而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和最终救赎,更解释不了那些突破性的事件将会是怎么如宿命般降临的。而这也才是虔诚而至信的阿尔都塞最根本的目的。于是最后他就不得不寄希望一个天降神人来力挽狂澜。
换句话说,阿尔都塞终其一生要完成两个辩护,第一个辩护,针对卢卡奇等之后黑格尔主义者,驳斥黑格尔那套精神历史发生学,并将其驳斥为一种神学,认为观念意识自身并没有历史,这种历史只是一种回溯性的自我误认的意识形态。第二个辩护,证明当下所处社会阶段必然灭亡,人类更高级阶段必然到来。并认为这是一种超越黑格尔派神学的新科学。这两个辩护的直接矛盾和冲突导致最后他出现了理论自身的断裂。最终不得不祈求一个理想中的罗慕路斯来力挽狂澜,建成罗马。
阿尔都塞借用的结构主义观念来自拉康,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可避免是葛兰西理想中的马基雅维利式僭主手段。这也是拉康派的宿命,拉康派的特点觉得意识形态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神鬼莫测,如蛆附骨。最后在对世界和未来的绝望中,只能靠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天降基督来制造奇迹。
用生产关系代替主体其结果自然是取消了之前西马主体理论中的敌我对立的斗争性,致使主体斗争湮灭于结构关系的不断生产与自我复制中。所以为了挽救斗争性,最后不得不又召唤回新的主体,但结果却是召回了一个施米特式的天降主体来机械降神,力挽狂澜。
这使得他们和现代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现代性普世观念一样,最后都殊途同归地不可避免地在一种由自身迷梦所制造的近乎永恒的“例外状态”中进入了波拿巴主义的陷阱 。
编辑于 2022-11-01 21:43・IP 属地河北查看全文>>
Virtua F - 59 个点赞 👍
查看全文>>
F-Hreinskilin - 45 个点赞 👍
单就反驳一下这位 自己阅读阿尔都塞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具体主张的观点,正好最近翻译的一篇文章可能与之相关,就引用一下。
从阿尔都塞的批评者那里拯救他
要论证阿尔都塞的作品对当代全球化分析和阐明不同的、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续相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阿尔都塞几乎受到了普遍的谩骂。8事实上,在分析当代世界政治和全球化时,对阿尔都塞的拒绝是一些更突出的思想流派的试金石:例如,在几乎所有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的著作中,"阿尔都塞的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再次被提起......"(Drainville 1994: 108)。在一个熟悉的自我和他者的逻辑中,对阿尔都塞和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的特定解读更普遍地有助于界定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最近,在全球化和更广泛的范围内,要求重振历史唯物主义的呼声。9对阿尔都塞的时刻及其更广泛的背景,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解读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推广这一术语的佩里·安德森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哲学、政治和文化等次要问题的形成,因而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不够。这是一种忽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 "压倒性地集中于对上层建筑的研究"(安德森 1976: 75)。这种上层结构的固定化,是政治失败的产物,导致了
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但这些从来没有被整合到一个关于其经济发展的一致的理论中,典型的是停留在一个有点超脱和专门的角度来看待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从一个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以某种理想主义来纳税。
(安德森 1998: 72)
因此,安德森称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最完整的完成",因为它把资本的"文化逻辑 "建立在欧内斯特·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描述上(安德森 1998: 72;詹姆逊 1991b;曼德尔 1975)。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复杂的死胡同相比,历史唯物主义对全球化的解释,似乎是通过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陈述,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分析(Anderson 1976: 94 and passim; Bromley 1999; Rosenberg 1996; cf. Harvey 1995: 5)。
安德森的论点既误解又低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成就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和其他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重新思考或克服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阿尔都塞 1984a, 1990a, 1990b)。10这使安德森的叙述的组织装置受到质疑。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看成是对上层建筑分析的主要贡献,误解了阿尔都塞对经济决定论的去中心化和对其他 "层次",如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分析之间的关系。
此外,安德森的论点,与其他试图反对阿尔都塞的人一样,取决于对阿尔都塞计划的高度可疑的解读。这种解读有一些特点,没有一个是可持续的。首先,阿尔都塞的作品被认为是与斯大林主义相勾结的,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或可能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但是,这种解读依赖于从政治实践到理论实践的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与阿尔都塞介入明确反斯大林主义的性质相矛盾,也与他对这种指控所假设的将理论实践还原为政治实践的持续批评相矛盾(Sprinker 1987:177-9).阿尔都塞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写出 "对......意识的条件和形式的真正历史研究"(1990a: 105),这是从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他在关于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的文章中对这种研究的要求也是如此(阿尔都塞 1984a)。
第二,阿尔都塞被指责为对意识形态和国家提供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无论其其他特点如何,都会破坏变革的可能性,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其他的。这里的批评也依赖于对阿尔都塞作品的误读。他关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文章是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功能性而非功能主义的说明,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再生产足以再生产资本主义本身的主体性(Lock 1988;参考Panitch 1996:87关于功能和功能主义)。然而,仔细阅读 "矛盾和多元决定"的读者会明白,这种再生产是无法保证的,而且由于下文要探讨的原因,这种再生产在本质上是开放的,会出现功能紊乱和颠覆。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 "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冲突"的 "多重"、"独特 "和 "相对自主 "的场所(Althusser 1984a: 23; Sprinker1987年的:194).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描述不是对失败主义和绝望的邀请,而是对武器的呼唤( Sprinker 1987: 229).11
第三,也是对任何声称是批判理论的作品最有害的,阿尔都塞的历史唯物主义被指责为结构主义,没有人类的位置。这一指控现在已经非常普遍,甚至成为教条,是安德森拒绝阿尔都塞的关键,也是伍德批评的核心(安德森1983:39;伍德1995:第2章)。然而,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指出的,在对资本主义的偏差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直接陈述中,是资本主义影响了(或试图影响)这个结果(见阿尔都塞1990d:237-8)。理解这种"可怕的实际还原"是理解英雄式的变革性集体能动性的(缺乏)潜力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阿尔都塞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涉及到将结构/能动性的二分法重新概念化为实践。在阅读《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时,需要记住阿尔都塞的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以及他对 "历史"和 "历史"中的主体之间的坚持。重点不是要消除主体性或能动性,而是要理解主体性和能动性形式的历史性。
我们认为,阿尔都塞的作品对能动性及其可能性条件的不同理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特别是在更多的唯物主义流派中,有着巨大的成果(如 Callari et al,.1995).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尔都塞的作品,以及更普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应该被看作是政治失败所产生的偏差,而是从经济主义的不足之处来解释政治失败的必要尝试。这些作品是"一个我们不能允许自己掉下去的门槛"(Hall 1985: 97)。12
重读阿尔都塞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该领域的其他立场一样,部分地是为了回应对阿尔都塞的特定解读,而我们对这种解读提出了异议。在寻求重新确认他的工作对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时,部分问题是 "阅读最好的阿尔都塞"(借用约翰逊1982年的话)。我们现在要做的正是这项工作。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阿尔都塞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重塑,其次是他对资本主义和主体性理论需求的说明。
超越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或者,唯物辩证法
如上所述,阿尔都塞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中引入了复杂性,他坚持:(a)生产方式的概念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即通过将其概念化为总的生活方式,而不是 "经济");(b)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别。一个社会形态是由一个以上的生活形式组成的。此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是社会形态,而不是理论化的生活。除了这些关键的概念区分之外,阿尔都塞还拒绝了基础-上层建筑中所隐含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模式,其方式将在下面讨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形式是以经济主义为标志的,这就是它与所有其他生产方式的区别。它必须寻求一个表达总体的实例化,其构成层次被纳入价值规律之中。它必须努力确保 "基础 "会得到它的繁荣所需要的"上层建筑";从不同层面的支持性实践的顺利运行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均衡性,而不是非均衡性,将是合适的。然而,对阿尔都塞来说,他同样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由于社会整体中因果关系的特点,即使在实际存在的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话案例中,资本主义也必然会产生 "不均衡性"而非 "表现性"。这里的不均衡性指的是不同的、可能是矛盾的逻辑在一个统一体中的共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虽然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一种殖民化的逻辑,但特定的实践层面的分离允许(至少是暂时的)逃离这种逻辑。对商品化的抵抗(或远离)是可能的,至少在短期内,而且与在经济之外的层面上进行的某些类型的实践有关。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将这些差异归入价值法则来寻求驯化这些差异,也就是说,通过确保它们发挥再生产资本的功能。因此,批判理论的一个任务是识别和鼓励反资本主义和/或非资本主义的差异的繁荣(见Gibson-Graham 1996),即使它承认资本主义在剥削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的同时,也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Lowe and Lloyd 1997b: 15)。不能假设差异会以一种同质的反资本主义形式出现,作为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者,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这样的假设是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明确的、系统破坏性的矛盾的想法提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警告我们,期待这样一个漂亮的简单的否定之否定是愚蠢的。
整体或社会整体的概念引导我们走向生产方式的扩展概念;其中包括一个内部关系的因果关系模式,涉及到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构成性的主张。此外,阿尔都塞提醒我们,生产方式并不是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的;相反,我们发现的是社会形态。如果我们要考虑到全球化世界中(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幸存"的可能因果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这种区分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1981:172;阿尔都塞1990a:特别106)。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化项目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它本身的矛盾性(这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简单矛盾");二是社会形态中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 "幸存者 "的持续存在。如果我们假设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力成功地制度化,我们将犯了阿尔都塞被指控的功能主义,而他自己也在理论上反对这种功能主义。简而言之,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形成,都没有像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那样发挥作用。那么,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同样的严格和全面的描述来完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描述是不够的。但这正是安德森对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论述的认可所暗示的(1998:72)。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要它假设现象学的形式可以从财产关系中衍生出来(如 Tetschke 1998),暴露了一个类似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逻辑。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这个禁用的隐喻,而代之以一个能够捕捉社会整体中因果关系复杂性的概念框架。13
阿尔都塞对发展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建立在他在《论唯物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概念重塑上,从而排除了唯心主义(意志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决定论或经济主义)。这些二元对立是将元素从社会整体(或整体)中抽象出来,并对所产生的抽象物进行重构的结果。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从人类实践的整体中抽象出来的,而人类的实践必然由思想和物质元素组成。从逻辑上讲,"经济"也必然由思想和物质元素组成。把经济和物质混为一谈,就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的实践归化为经济的特权,从而带来危险。资本主义寻求一个经济"决定"所有人类实践的世界。基础-上层建筑试图解释的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新现象,但其方式是不加批判地接近其研究对象。与这种非常简单的,甚至是简单化的解释手段相比,辩证法涉及到对一种分化模式的理解,这种分化涉及到原始统一体在空间-时间上被分割成内部相关或相互构成的元素。正是这种相互构成的碎片化产生了矛盾。理解由此产生的矛盾的整体性,需要超越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所特有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发展;因此,阿尔都塞拒绝了停留在二元对立的理论世界中的"颠倒"隐喻,也因此强调了实践的概念。基层-上层建筑的隐喻鼓励我们从外部的因果关系模式来思考,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涉及到社会整体的必要元素或层次的概念化,作为实践之间的内部关系(也见Ollman 1976, 1993)。
就其本质而言,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具有二元对立的特征,并推动了分析性思维而非辩证性思维。也就是说,它把我们推向了自由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它最清楚地揭示了经济主义——也就是将经济决定论具体化的政治企图,这是资本主义的识别特征。然而,与此同时,这个隐喻掩盖了这种经济主义在历史文化上前所未有的——即文化上的偏差的性质。它通过将历史文化的自然化而扭曲了。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经济主义是理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通过以自然主义而非批判的模式代表资本主义实践的一个构成要素来表达资本主义文化的常识(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1970:第4章;阿尔都塞1990b)。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促成现有社会关系的转变,而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复制,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改革。我们需要清楚,经济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表现,而不是人类生活的普遍事实。此外,它的相对成功需要国家主导的文化转型(参见Corrigan和Sayer 1985)。但是,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的生存还需要国家主导的行动,将资本主义从自身或从经济主义中拯救出来。此外,正如阿尔都塞使我们理解的那样,即使在明显完成的地方,也会出现矛盾的实践,这些实践可能成为颠覆该经济主义的基础。关于阿尔都塞对精神分析的有争议的概念性借用,在这一点上将是有用的。
矛盾和多元决定
为了寻求一种足以应对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矛盾整体的特殊复杂性的因果关系的解释,阿尔都塞转向了精神分析,在那里他找到了他的主要理论创新的来源,即多元决定的概念。不幸的是,他没有将他的借用理论化,从而给他的读者留下了一些困惑,如果不是直接拒绝的话。14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然而,需要非常有力地指出的是,多元决定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原因的多元性,正如一些著名的阿尔都塞评论家所建议的那样(例如Callinicos 1976, 1993)。与多因性(multicausality)相反,多因性意味着外部相关因果因素的多重性,而多元决定则涉及一个由矛盾的和内部相关的部分组成的整体中的复杂因果过程。吸引阿尔都塞的是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概念,它在捕捉复杂的因果关系过程方面很有成效,这个过程在一个矛盾的社会整体中发挥作用,这个社会整体由多个不同的、但内部相关的、相互构成的实践组成,由于它们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的时空分离,有一种渐行渐远的趋势(见马克思1951:383,关于这里解释的矛盾的概念)。这意味着,经济本身不能用自己的资源来生产它的再生产手段;政治或意识形态也不能。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能决定任何东西,甚至这样说也是胡言乱语。决定性意味着外部相关实体之间的简单线性因果关系模式。虽然这种因果关系模式会在社会整体中的局部领域被发现,但它不可能在社会整体本身的层面上涉及,就像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会让我们相信的那样(Jameson 1981: 25)。正是因为世界是多元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所以未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或者,正如巴里巴尔所说的,多元决定 "是历史的奇异性所承担的形式"。巴里巴尔 1996:108).
这种激进而富有成效的因果关系的重新概念化是承认人类生活必要的多样性,同时使我们能够识别可能会失灵的多样性的形式——以解放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而言。多样性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于一种特殊的内部相关层面的实践的分裂,使这些实践能够发展(至少在短期内)"好像"它们是自主的,因此是相对自主的。相对自主性是一种从必要的实践的时空分离中出现的条件;它是一种从必要性和矛盾性的共存中产生的社会逻辑。相对自治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同"层次"的实践——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同时联系和分离(实际的相互依赖和表面的独立)的因果效应和政治可能性理论化。因此,它使变革的能动性的理论化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差异而非同质性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属性。
对阿尔都塞来说,作为"纯"生产方式的社会整体只能作为"逻辑"或思想对象存在。在经验世界中,"纯"社会整体的不均衡性在社会形态的形式中得到了加强。我们有阿尔都塞对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社会形态的分析作为这种情况的说明(阿尔都塞1990a: 19)。阿尔都塞使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同时达到几个目的。首先,它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了社会形态的特殊矛盾的动态,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矛盾。第二,它说明了一种基本的破坏性(即各层次之间的功能关系的解体),它提出了历史变革的可能性。第三,它构成了对经济主义的理论错误和政治危险的警告。在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经济主义的分析决定了一个革命方案,即在假设必要的,即社会主义或彻底的民主的"上层建筑"变革将随之而来的情况下,把生产关系的改造放在首位。15在这里,如果不特别注意文化领域,就会导致共产主义项目的颠覆,因为"幸存者"的因果关系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权相抵消。以其他方式表达,由封建社会关系构成的主体,即农民,很容易接受并支持一种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形式。16
阿尔都塞在他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中对主体性的去自然化,集中体现在他对意识形态作为所有人类生活的一个必要元素的重新认识上。17归纳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忽视的是,人类需要意识形态的构成;事实上,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人类。因此,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阿尔都塞 1984a: 33)的说法被误解了。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性的抽象",因为它指的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遍属性(马克思1973b:85)。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是意识形态的创造者(阿尔都塞 1984b: 154, n.2)。如此定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力量和意义的结合,因为它们由社会关系和实践的纽带组成,有能力将人类构成为拥有历史-文化特定处置、技能和能力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那些将自然的 "将要被人类化"的人构成为一种特定的主体的实践(阿尔都塞 1984b)。正是主体性形式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反过来产生了特定类型活动的能力。行动的形式(实践)是由文化赋予的。反过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实践的必要多样性和矛盾关系是新的非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实践的来源。对阿尔都塞来说,国家的职能是确保这种实践不出现或不繁荣,因为"科学"或批判理论的职能是帮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非自然化,以帮助社会主义转型。
因为主体性是历史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因为社会整体的特点是多元决定而不是决定,所以经济主义作为对社会的解释,以及对根本性转变的方式的解释,必然是不充分的。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未能关注主体重构的文化任务,导致苏联未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所期望的激进民主。斯大林主义是经济主义分析的结果,它对主体性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同样,对斯大林主义的回应,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因假定存在正确的主体性而重复了这个错误(阿尔都塞1990c)。由于这个原因,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两者都没有产生对主体性形式的历史文化特性的理解,因此也没有产生对特定类型行动能力的理解。简而言之,将主体性视为理所当然,必然会导致对革命的颠覆。这就是阿尔都塞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试图向他的共产主义同伴传达的信息。那些主张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尤其是考虑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形成的模式,假定唯一"真正"的斗争是那些采取阶级形式或涉及工会主义的斗争,只是错过了全球化背景下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形式的多样性,并将马克思主义者与之隔绝。这并不是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经 "死亡"——远非如此,而是坚持通过阿尔都塞的进步所提供的视角,再次重新阅读其文本的成果。现在,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形式,有可能参与到由貌似全球的资本主义发扬光大的经济主义的再生产中。
正如Resch(1992年:第4章)所显示的,由阿尔都塞发起的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已经开发了各种工具——概念、理论和方法用来进行主体性分析。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在这些文献中,最突出的是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女权主义学者的工作,他们以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忙于与关于主体性的最好的资产阶级学者接触,实际上是把它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上带走。18这项工作特别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它为历史唯物主义拯救了主体性的概念。它还对那些认为围绕性别和其他形式的身份政治组织的斗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理论之外必然低于更基本的阶级问题或与之对立的斗争的人提出了直接挑战。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引起的文化斗争的非无产阶级性质,创造性地阐述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的例子也在其他地方迅速增加,为建立一个灵活时代的灵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阿尔都塞之后的全球化:理论的政治性
如果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全球视野确实是更新的马克思主义项目的预兆,我们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哪种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一个解释能力和批评洞察力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全球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我们如何将经济和主体性理论化的问题。阿尔都塞的工作对发展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和加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批判理论的说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它提供了产生一种批判性理论的希望,这种理论注意到政治经济学的相当适当的关切,而同时又不会对差异的重要性和相对自主的因果力量视而不见。这将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它既不通过将差异还原为政治经济学,也不通过完全拒绝其重要性来进行。相比之下,最近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因素则两者都有。那么,前进的道路是与阿尔都塞手拉手,而不是没有他。
任何试图从众多特殊的斗争中组织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尝试,其中许多甚至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是问题,将需要讨论
共同性/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一个的特殊性和另一个的普遍性。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如何运作、社会关系如何展开、人类潜能如何实现的另一种看法,本身就成为概念工作的焦点。
(Harvey 1995: 15)
在不否认在知识工作和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的情况下,"创造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们面对新的世界秩序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Callari et al. 1995: 4)。在寻求通过一开始就排除一些马克思主义来约束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可能启动一系列的实践,这些实践将告知并塑造我们集体创造的未来。最重要的是,这些未来将反映这种对差异的否认。在试图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并且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要找回哈维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的那种多元主义就会更加困难。这些问题也不能留到"革命之后",或留到代替革命的任何东西。正如Cynthia Enloe(1989:59-60)所指出的,在1920和1930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妇女地位方面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即身份和差异。为了团结和运动的利益,妇女们压制了这些问题。几十年后,当该党最终掌权时,妇女却没有出现在其领导层。越南独立后公共生活的男性化,以及国家愿意将年轻女性的身体作为商品提供给国际资本的代理人,如耐克,部分是这种压制差异的副产品。
在我们考虑如何在冷战后和面对全球化时重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值得反思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经验。在本章中,我们强调了一系列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差异的问题,并试图将这些问题与革命主体的生产问题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我们建议,作为一种经济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具备处理此类问题的能力。与Andrew Gamble一样,我们同意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而精辟的批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帮助我们想象对当前世界体系的激进替代方案,那么,也许它必须愿意放弃对革命实践的主张......废除自己作为未来理论的地位"(Makdisi et al. 1996b: 12)。全球化,无论是作为一个项目还是作为世界政治的新现实,都迫使我们批判性地参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世界的解释的合理性,参与其政治想象力的限制,从而参与其作为一个政治项目的适当性。这使我们直接回到安德鲁·塞耶(1995年)和J.K.吉布森·格雷厄姆(1996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解释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怀疑,并在他们之外指向大卫·哈维(1995年:15)的呼吁,即建立一个能够将我们之间的分歧阐述清楚的社会主义先锋派。我们认为,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处理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开始勾勒这些问题的轮廓。路易·阿尔都塞有争议的遗产不是一个障碍,而是在这场为灵活的时代建立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必要的帮助。
发布于 2022-10-29 21:14・IP 属地广东查看全文>>
庸人道士 - 34 个点赞 👍
我的评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是我写的笔记。
我慕名而读,但是读完以后,感觉没有那些人吹捧的那么好。
首先这本书的确有一些优点,优点就在于好读懂。
接下来,我说一下这本书的缺陷,
首先、我认为这本书作为哲学书是不合格的,他的论证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为什么这么说?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甚至于在最后一章之前的所有内容,都是在重复马列主义中我们所熟知的内容,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并且阿尔都塞特别喜欢这么说话,如引用一段马克思或列宁的话,于是就说这段话精辟地指出....,或者说这段话使得....化为齑粉,然后就接着论述。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里的论证基本上都在诉诸于权威,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能读起来非常酣畅淋漓。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前面那么长的铺垫,对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论证就相当于安瑟伦的上帝论证,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安瑟伦的论证似乎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安瑟伦的论证一文不值。
其次、这本书所透露出的思想,具有不可证伪性。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具有意识形态性,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不断地再生产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并且把它贯穿在方方面面之中,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传媒,乃至于他认为工会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压根就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这样的做法。我能说服阿尔都塞吗?
不能,因为阿尔都塞可以这么反驳我,你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洗了脑了,却不自知。这样一来,我就哑然了,我似乎任何的论证在他面前都变得无力。
这就是这本书思想的最大问题,具有不可证伪性,或者说与阴谋论的论证本质上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认为,假设存在着蜥蜴人统治着地球人类,但是人类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蜥蜴人再生产他们的权力的一种工具。并且我认为,所谓宗教、战争、科学,都是蜥蜴人发明出来,并且暗中灌输给人类,让人类不知道蜥蜴人的统治。
那么我如何能够反驳这种阴谋论论调呢?答案是,绝无可能去反驳,因为任何的反驳,在他们眼中,要么是被蜥蜴人洗了脑了,要么就是为蜥蜴人做事,大白话说,这叫做非蠢即坏。
而阿尔都塞这本书洋洋洒洒400页,其实核心观点就是如此的粗糙。
并且,我们似乎还可以这么质疑,如果说你认为,连工会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你现在所写的这本书,毫无疑问在法国出版了,那么是不是也是资产阶级洗脑我们人民群众的武器呢?否则法国的资产阶级怎么就能让这本书出版呢?真可谓是大伪似真啊。
所以阿尔都塞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此处。
并且,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论点,就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存在经济危机的,而经济危机的来源在于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在的问题在于,连对于资本主义生命攸关的经济危机,都是因为无政府状态引发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又能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呢?如果他能够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摆脱经济危机呢?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承认这样的论点,而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却恰恰提供了这个论点。因为阴谋论体系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设想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力量缔造了诸多麻烦,而这个力量自身又无法消除。这是自相矛盾的。
三、阿尔都塞思想之中的极权主义因子。
阿尔都塞通过分析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生产意识形态不断地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革命家要剥夺资本主义的剥削,那么必然要打碎所谓的意识形态机器。那么怎么打碎?
似乎阿尔都塞在这本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的确说到必须打碎。首先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打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尽管他没说,但是历史上有人试图这么干过,那就是中国人饱受折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剥夺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
结果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谓极权主义一个典型标志,是思想罪的提出。黑格尔认为,普通的刑法是不会深入到人的思想领域,当一种权力深入到思想领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种思想罪,而这种罪,就使得一切都陷入到权力控制之中了。
而如果你要打破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你的做法实际上就必须通过这种思想罪的方式,宣布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维护者,把他们肉体消灭,或者人性的改造。这样的方式,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才具有的模式。
并且,阿尔都塞认为,家庭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一部分。那么毫无疑问,似乎家庭也要被拆散,通过一种外在的方式清除这种意识形态,结果怎么样,中国人都知道。
阿尔都塞的理论,基本上继承了列宁的民粹主义思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所认为的群众的优先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是群氓,他们比资产阶级骗了,所以必须让一些先知代替群众思考。
所以一言以蔽之,这本书的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最后那个论意识形态,无非是化用了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及拉康的一些说法,目的就在于通过建构论的方式,实现一种不可被证伪的自循环论证。
编辑于 2022-10-28 19:23・IP 属地吉林真诚赞赏,手留余香还没有人赞赏,快来当第一个赞赏的人吧!查看全文>>
林先生 - 3 个点赞 👍
引用自阿尔都塞,《论再生产》第六章,吴子枫译本。(标题为本人所加)
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摧毁了资产阶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最重要的部分后,列宁仍忧心忡忡。从他这种悲剧性忧虑当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仅仅摧毁镇压性机器还不够,还必须摧毁并更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不然,危及的是革命自身的未来。……要替换旧的AIE…困难重重并极费时间。比如,要真正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系统,一套全新的工会系统,一套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系统,需要很长时间。首先必须确切地知道要建立什么,要发明①一些怎样的新系统,以及如何建立它们;必须为这些系统中的每一个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且要深入到各种细节当中;最终,必须培养一批既能干又忠于革命的人,以在每种新的AIE中实行革命的新政治,总之,通过每一个苏维埃公民的事件和觉悟过渡到新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如果最终没有完成上述任务,甚至没有严肃地谋求彻底地(不带任何让步地)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旧的(资产阶级的)AIE会整个地或部分地保持不变,或几乎不被动摇。在新的制度形势下,如果有旧有人员保持不变,无论大家做什么,无论大家的打算是什么,旧模式的AIE——无论是完好无损,还是经过不完全的改造——都会继续其先前的“工作”。旧AIE的一六部分实际上不少想群众反复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少让庞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它们应该成为新的AIE)发挥功能,而是继续向群众反复灌输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甚至在人们给它们提高了新的成分作为反复灌输的命令和任务的同时,已然反复灌输与之相抵触的旧意识形态。
在这件事情上,憎恶各种“政令”的列宁完全清楚,“政令”不能解决问题,哪怕它来自高层。他也清楚:要建立新的AIE,不存在先天的、事先完全准备好的计划和路线;这是一件每时每刻都要做的工作,更确切的说,是一项包含巨大风险的漫长实验,必须投入全部智慧、想象和政治忠诚;这是一场不容丝毫懈怠的斗争,是异常不能只靠有限的行政手段,而要靠深入细节的智慧,靠教育、说服和耐心的解释才能完成的斗争;这是异常不能靠少数战士——哪怕他们非常清醒非常勇敢,而是要通过求助于群众、求助于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反应、他们的首创精神和他们的发明,才能完成的斗争。
如果这场斗争不能获胜(它当然无法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事件里就获胜),甚至如果不少在正确的群众政治的基础上真正严格地获胜,它就会严重地限制乃至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
如果不幸,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少越来越纯粹地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发挥功能,而是继续通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或者通过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混合物”来发挥功能,如果旧的摄像头没有被根除,那么,谁能向我们证明:甚至在社会主义(形式上的官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的表面下,不会是旧的意识形态得以维持原状、进行自我再生产、并导致那种极端危险的后果——即旧的意识形态完全钻入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或政治关系的种种缝隙中——呢?
如此一来,苏维埃会怎么样?工会会怎么样?无产阶级教育系统会怎么样?
当列宁如此经常地暗示,并且是以悲剧性的郑重警告的词语,暗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残余”的危险,暗示“传统”、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沉重负担时,他确实早就已经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小生产”的残余和复活而得到了再生产。
……这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在无产阶级新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命运,还没有得到解决,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列宁在还未能确保这些决定性的问题得到解决前就去世了。
他把它们留给了自己的继任者,斯大林。斯大林解决了这些问题吗?
在苏联,斯大林之后,苏维埃、工会和无产阶级教育系统,今天怎么样了呢?
如果斯大林忽略了这些问题——正如大量的后果…使人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自那以后,这些问题也没有重新得到严肃而彻底的研究呢?为了直抵我们忧虑的根本,我们要说,难道不正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才能解释当前左右着苏联的政治、左右着它的困难、左右着它的“计划化改革”难题、甚至左右着它的某些绝境……的大部分原则吗?编辑于 2023-02-27 21:01・IP 属地广东查看全文>>
汪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