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个问题的回答下,很多人对《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是二本学报这事冷嘲热讽,这实在是没必要。虽然整体上高校学报的水平与学校层次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二本学校也不是办不出好的学校,甚至一些职业学校也能有好的学报,如《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就曾经是C刊。要说论文的好坏,还是就事论事,看出身没多大意义。
具体到论文本身,整个文章比较大的问题,一是样本量少,且未能说明样本的代表性何在,二则是整个论文为结论找素材的情况较为明显。其实在整个论文中,能看到很多矛盾的地方,这都是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如这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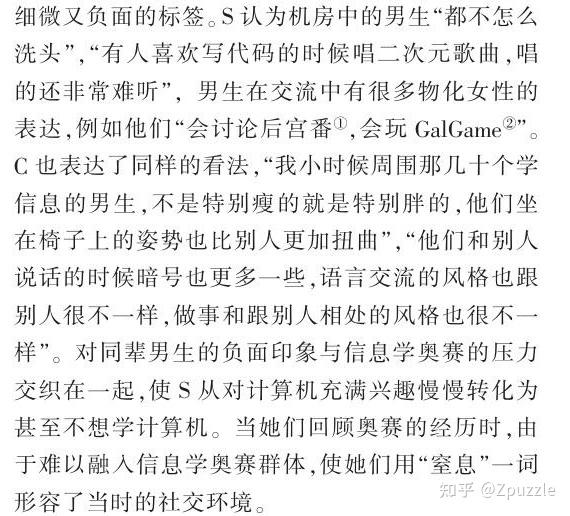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在这个反馈中,女性对男性的负面印象来自于“他们不怎么洗头”、“唱歌难听”、“讨论后宫番”。但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讨论后宫番这些问题可能因为存在物化女性而让女性心理不适的话,那么从外貌、穿着、爱好等方面来否定男性,又显然与后面的这段话完美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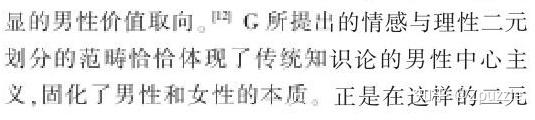
虽然我没读工科专业,但就我对男性的了解,在涉及专业知识的问题上,大多数男性能做到就事论事。比如,对于一个男性,如果你跟他说“你要去的这个科研团队,女同学长得都不好看,也不爱打扮,男同学不是特别瘦就是特别胖,你最好还是别去了”,他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因为男性在专业领域普遍是一个以专业能力为第一评价标准的思维,比如前些年曾引发争议的张昆伟:

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是著名的“姚班”学生。后来,他曾发过一个征婚广告,结果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中,对清华和姚班较为了解的业内人士,都认为这是个专业水平很高的人,但是大多数的女性却因为他的外貌在第一眼就否定了他,甚至对他的相貌进行恶意攻击。
假如,对于一个想学计算机的人来说,此人是团队内的大师兄和导师之外的总负责人,我觉得男性大概率是无所谓的——反正我来这儿是学技术的,别人长得好不好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恐怕一些女性就会劝退,“跟这种人当同学,朝夕相处,真的是没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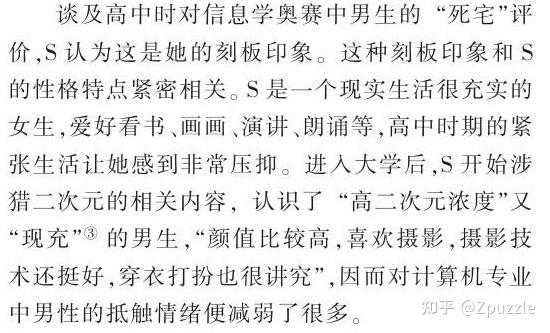
当然,在以男性为主体的行业中,女性的确不容易参与进男性的社交圈子,这也被认为是影响女性职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个访谈中也清晰地展现出,在女性选择专业和职业的过程中,“非技能因素”的评价占据了更多的比例。
至于女性为何会将非技能因素的评价置入于工程学科这样更强调专业技能的学科中,一种解释是,女性的生活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打扮自己,所以他们也会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异性,而这又涉及到了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训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恰恰是这种以非技能因素进行决策的行为,阻碍了一部分女性去以专业心态接受专业教育。
男性并非不喜欢漂亮的异性,但是长期的性别规训和职业分化,让很多男性都不会用非技能因素来在职业领域内进行决策。简答一点说,就是绝大多数男性都愿意去跟一个长得丑的大牛学习,而不会去跟一个技术菜的美女学习。
这个文章也提到了社会期许的问题,即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往往并不是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才,而是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很多女性也会放弃在技术方面的学习。此外,还有之前说的性别环境等差异,那个已经是研究很久的方向了,这里面并无新意。
总的来说,仅就论文中呈现出来的访谈内容来看,可挖掘的点就有很多,但作者选择了忽视这些内容,而仅挑选能印证已有观点的内容来进行论述,最终导致的问题就是论文的逻辑性问题比较明显。而从这篇论文来看,也能看出一些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困境:她们一方面意识到了规训的存在,像摆脱被物化和被凝视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她们又热衷于接受规训给他们带来的思维模式,用主动地“选择”(即通过评价男性的外貌、行为等进行择业、求学等)来达成伪自主性。于是,哪怕是在工程技术这种强专业知识导向的学科里,外貌、行为也能影响一个女性的职业选择。
如果再往深一点挖,为什么在这些强技术导向的学科里,女性依然会有大量的非技术因素进行决策,可能的一点理由是,女性对自身外貌的关注与择偶有较大关系。这反过来也与前面所说的对应,即男性在情感与专业知识方面会进行分离,择偶是择偶,专业是专业。一个男博士娶一个美女本科生会被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一个女博士嫁给一个男本科生——即便双方情投意合,也会被认为是有点别扭,甚至很多女博士一开始就会拒绝与男性本科生谈恋爱。
这就又涉及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智性恋”。尽管这个概念本身漏洞很多,但有一点倒是确定的,就是女性要求的“智性恋”,男性必须在外貌和学历/知识方面都过关。如开头提到的张昆伟,虽然毕业于清华姚班,但很难成为“智性恋”的主角,女性塑造的高知分子形象也往往都是外貌与知识兼具。
以上这些顺着主题深挖,或许都有更多的阐释空间,但相当多女性主义者的思维已经固化了。当下相当多的女性主义者,脑海深处依然是“被拯救”的思维,即认为“社会压迫女性,只要没了这些压迫,女性就能自由”,但却并不考虑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自身可以发挥什么样的自主性(如改变以非技术因素选择技术专业的思维)。而这种“被拯救”的思维,在公众舆论中也呈现出一体两面的特点:一方面,其会将所有的矛盾都归罪于男性和社会的压迫,极端一点就是“打拳”;另一方面,则将女性可能的反抗,全部集中于“抗议”和“指责”,忽视了女性自主成长的可能。而这大约也是无论国内国外,女性主义虽然声音很响,但在执行层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