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是旷野,而是典中典

这句话的全句是: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
不过由于概念的多义性,导致三位老师后面的回应本身是从隐喻结构去重新解释的。
刘艾奇说,人生是海洋。
熊浩说,人生是地球。
沈奕斐则说,旷野这个说法背后有一个有一个港湾或家的存在,才让旷野具有了美感。
然后讨论很自然地转向了旷野和月光哪一个更容易寻找上。
如果是站在一种建筑学的角度出发,月光和旷野可以被认为是同义词。因为月光也是一个相对私密的、不被发现的空间,而旷野同样如此——在旷野里,自然人生就只有你一人,而不是其他的空间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看,把抽象概念具象化为某个具体实物,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美学的做法。乌托邦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人们把对理想、自由、完满的概念都附着在一个与世隔绝却相当完美的岛屿上,并且为这个岛屿赋予了更多意识形态的解释。
于是光谱从父性的乌托邦也就逐渐转变为母性的敌托邦。
这其实也难怪,因为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嘛,人毕竟是活在三维世界里的生物,最能理解就是两种东西,一种是自我身体,另一种就是空间结构了。
那么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对应: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这里的轨道对应的就是那个一直被提及的“社会时钟”,就是按照某种预设的既定的生活、工作方式的需求而进行的过程。而且轨道还意味着,对于我们人来说,人生的未来选择,在没有新轨道这个说法的前提下,就是几乎可以望到头的。
那么它会带来什么呢?答案是,除了带来机械、重复、单调等一系列极度后现代扁平化的体验之余,还能带来“稳定感、安全感、结构感”。
这个比喻有一个遮蔽,这个遮蔽会让我们陷入这层比喻里而不可自拔。那就是这个人生的定语到底是什么?是“我的人生”还是“我们的人生”呢?是具体化的、个别化的人生,还是概念化的、群像化的人生呢?不知道,但很明显是前半句诉诸于个人(旷野),而后半句诉诸于群像(轨道)。
所以说“所有的类比都是不当类比”。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生是(我的)旷野,而不是(我们的)轨道。
不过你说艾奇讲人生是海洋不对吗?当然对,是对同一个空间的二次隐喻。
旷野与海洋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旷野没有目的地,而海洋似乎存在某个会抵达的彼岸。
既然有目的地,那么看起来海洋就要比旷野更友好,因为彼岸的寻觅是可以通过勾勒的方式去再度追寻的,是完全来自个人所想要找到的——或者没有结果,只有过程的东西组成的。
既然都这样了,那东浩纪就应该登场了,所谓“哲学的观光客”就是把当地村民和游客两种身份之间再切出第三种身份,他们会把自己原本熟悉的身份营造出一种陌生感,变成用“别样生活”的方式再度重新观瞻自己:
1. 村民:只在单一的共同体中生活和思考的主体。对于主体来说这里只有熟人。
2. 旅行者(traveler):不断地游走于各种共同体的主体。这里只有陌生人,也就是“他者”。
3. 观光客:生活在特定的共同体中,但是也会时不时的去其他共同体的主体。这里既有熟人又有“他者”。
我们似乎应该主动去寻找误配,这就回到熊浩所说的 刻意逆反的闲暇 方式了。
既然身份体验可以被重置陌生化,那熊浩说的“人生是地球”听起来就显得更“土”又更“真”了。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地球:
在地球上除了旷野以外,那还有山川,还有高原,还有荒漠,这都是人生可能会经历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象人生是旷野,就是我们歌颂了人生当中充满自由的那一个部分,并把它当成人生的全部的时候。其实你建立了一个对人生并不完整的预期。
这就是放弃了 众所周知 的隐喻,从而发展出一种对当下已经熟悉的场域的再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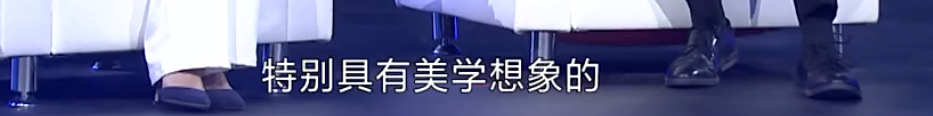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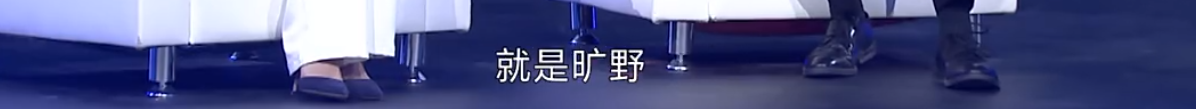
熊浩说:“大世界中特别具有美学想象的就是旷野”。
作为美学学科研究者,我认为这里的美学想象其实并不是它具有某种独特性,而是因为旷野失去了原本的空间隐喻,变成了一种“百变怪”式的平台,它不再是场所,而是平台。旷野的想象力就在于,它的本质其实是废墟,废墟之上万物可生——而废墟被赛博化之后,就是平台。从古希腊的平台,到现代的剧院和电影院,再到后现代的网络,都可以非常轻松得剥离掉一切正在表演的东西,又回到旷野这个概念上。
所以我觉得,人们向往旷野,或者说觉得人生是旷野,是一种非常年轻态的思考方式,似乎永远都可以重新再生,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漫长的破坏和重建过程的前提下,在旷野上以数码的方式叠加出一个新的空间。
这在物理世界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牛马土木劳动者,不被人看到的劳动群体们的生活模样——就像“大猛子”在B站视频里对一线建筑工地的建设过程的最直观的表现一样,而他最后也成为了高度相似《黑镜-一千五百万的价值》里黑人小哥的追随者。
但是在赛博世界,这件事就是家常便饭——诺齐克就曾在 元乌托邦中讲述过相似的话,因为元乌托邦是平台,所以平台本身不会生出任何乌托邦想象,只会生出更小的、更细致的、更鲜活的乌托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