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不就是迁都洛阳了吗?虽然没有立太庙、没有法定称京师,但实质就是迁都洛阳了。谭其骧历史图集的隋朝全图,就是以东都为首都标识的。怎么这个时候大锅在身,一些网友就不强调隋炀帝迁都洛阳了呢?
因为结果已经显现,迁都了,然后亡国了。
先是杨玄感围洛,然后李密瓦岗军围洛,然后宇文化及围洛,然后王世充据洛,然后李建成至洛,然后李世民唐军围洛,然后窦建德来洛,然后唐军平定洛阳...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粮食?四战之地够遭几回劫?各方军队就像老鼠见着敞着的肉一样围上来,主要就是劫粮仓。
东都,放篮球队里,就属于最佳第六人那个性质。时均数据很耀眼,不代表可以耀眼得打满全场。主力打久了累了,最佳第六人上,而且能够很好得承担镇场责任。等主力缓过来了,然后最佳第六人下。这就是最佳第六人的作用。可这代表最佳第六人体力好吗?要让最佳第六人作为首发一直在场上,他根本撑不了主力在场上这么久。
关中动不动就饥荒,是因为长安城的脱产人口太多了。有这个脱产人口,就饥荒。因为本地粮食加外地漕粮不足以供应庞大的贵族群体、官僚群体和京师军队。但如果没有这个都城附加庞大人口,同样的灾年就不是饥荒。
韩愈在唐德宗时代就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长安不啻百万人口,唐德宗是什么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吐蕃之乱、二帝四王之乱连续打击,人口跌入中唐低谷期的时代,长安就百万人口。那唐高宗到唐玄宗前期的唐朝全盛期,长安到底得有多少人?
脱产人口太多导致的饥荒,去洛阳的原因就俩:
1、洛阳人口少,作为粮仓能替长安减压。
洛阳河南府人口在全盛时也只有长安京兆府的三分之二,人少。这还是武则天迁了关中十万户,至少四五十万人到洛阳的结果。唐朝更多时期,洛阳人口只有长安的一半。毕竟城池规模也就是一半。洛阳的脱产人口少,粮食消耗小,皇帝和百官去洛阳,能缓解京师的耗粮压力。这是给关中减压的行为,可不是什么关中凋敝,洛阳繁荣的结果。
恰恰是洛阳不够繁荣,人口和粮食的配比没有饱和,才能成为关中的替补和过渡,它如果和关中一样繁荣,皇帝去了是一样的粮食危机的结果,那就没必要去了。何况洛阳也不是没有天灾,不是不会遇到饥荒,只不过长安和洛阳一起闹饥荒的年份毕竟概率小,巡幸是利用概率错位避免粮食危机加深。洛阳的粮食是运河的漕粮,也不是洛阳本地的粮食。洛阳虽然运河能通达,可以囤积粮食,但洛水容易泛滥,也动不动就闹水灾。但两京一起遇到灾年的概率小,不代表一定不会发生,也终归遇到了。事实上唐高宗晚年一次去洛阳时,饥荒几乎是从长安到洛阳整个两京之间都在死人。
所以替补上去也要看情况,长安闹灾,洛阳不闹的时候,去洛阳,可以缓解长安压力,给予洛阳特殊待遇,皆大欢喜。要不然唐高宗临死那天还在洛阳大赦,洛阳老百姓很高兴。高宗问官员,听说洛阳百姓得到大赦很高兴,来了句:“洛阳百姓是高兴了,我的生命却快油尽灯枯了,要是老天爷再给我一两个月的时间,让我能回到长安,我才能死而无恨。”唐高宗这是临死抱怨呢——洛阳人是高兴了,我却遗恨到死了。
长安闹灾,洛阳也闹灾的时候,咋办呢?还是去洛阳啊。减轻关中的压力就是洛阳作为东都的第一使命。都闹灾,那也只能优先死洛阳人,尽量减少死长安人。所以高宗晚年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道路堆满了死去的灾民尸体时,他还是毅然决然得率百官赴洛。两京之间堆满死人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就是皇帝车架沿途所见。明明两地都在闹灾,他也得硬着头皮去祸祸洛阳人。长安才是家、才是宗庙所在、才是京师、才是自己未来的坟茔、才是统治集团的大本营所在。
所以去洛阳是太平时期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但要迁都到洛阳,那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王世充、窦建德、李唐群狼撕咬的四战之地、亡国命运、前车之鉴,就又该上演了。唐高宗和唐玄宗唯二主动巡幸洛阳的皇帝也不傻啊。难道人家皇帝不看历史吗,何况前车之鉴还正好是人家的“建朝史”。我就问现在有谁把民国政策路线奉为圭臬的没?那是经验还是教训?
2、运河在三门峡砥柱山这块有漕运拦路虎,所以运河技术瓶颈不解决,只能先去洛阳。
三门峡砥柱山,在唐朝是一群明礁加暗礁,漕船很难通过。李渊开始到李治,长安人口少,所需漕粮不过一二十万石,所以没想着要解决这个漕运的拦路虎。漕粮一般是从黄河进了洛河,然后卸货到洛阳含嘉仓,再从含嘉仓经过陆运送进潼关或者直接陆运送到长安。
到了李治中期,长安人口暴增,漕粮需求暴增,脚力消耗太严重,成本过高,这才想着要解决关中的粮食危机。
但李治和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斗得很厉害,所以就越过三省的正规程序直接手诏升格洛阳为东都,用巡幸洛阳当做牵制关中的关陇集团的方法。所谓的长安粮食不够吃,只是李显跟洛阳搞暧昧,制衡关陇集团的一个理由。理由,和原因,这两个词有时候重合,但有时候不重合。理由有时候是借口,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
不过后来关陇集团已经被打压下去了,但武则天又借洛阳和太子时常独立监国和经营的长安朝廷斗,还把太子给毒杀了,所以后期李治也受制于武则天,实际上李治到后期是时候应该正面解决运河问题,却受到牵制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通过继续巡幸来回避运河问题。
武则天死后,没了掣肘,加上李显重用韦皇后身后的京兆势力,就着手正面解决运河问题了。但李显的方案是走江汉漕运,把粮食从汉江和丹江运到商洛,然后从商洛经百里水陆中转进灞水直抵长安。不过李显在位时间不长,政策没有足够时间落实。而且李显后期有所动摇,对韦后开始不信任,最终被韦后所弑。李显一死,这套方案又被废弃了。
李隆基上台后,因为要打击韦后背后以京兆韦氏为首的关陇势力,否定中宗李显执政路线,于是他倚仗关东的宋璟、张说等关东出身的武周遗臣,宠幸武氏妃,继续搞高宗那套两都巡幸以渡过灾年的方案。但最后他自己都烦了,在开元后期搞改良运河。等于是在掌控了整个局势后,要直面问题,解决运河瓶颈。
李隆基的方法简单有效——三门峡不是有砥柱山吗?那把砥柱山这一段中转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进洛水,让洛阳当粮仓然后经过三百里陆运送到潼关呢?为什么非要洛阳掐住长安的命脉呢?只把砥柱山这一段中转不就可以了嘛?
然后,大部分漕船不再进洛水,而是直接奔向砥柱山,然后在砥柱山跟前卸货。越过砥柱山十八里,然后再装船重进黄河,从黄河进渭水直达长安。
三百里洛阳到潼关的陆运,变成砥柱山那一小段十八里陆运,就这么简单,从此以后洛阳就开始不可逆的衰落了。加上安史之乱时再次沦为战场,洛阳在乱后户口更是十不存一。
其实饥荒年份也只是少数,一般只要够积贮京畿两年的粮食,能够稳定渡过灾年,皇帝也是不想到处跑的。唐朝前期皇帝由于运河不畅,长安没法囤粮,属于“月光族”,漕粮来了仅够当年吃,还没等大规模饥荒发生皇帝就先去洛阳,以防万一了。从开元后期漕粮不再绕道洛阳后,基本上皇帝在长安都能囤个够吃一两年的粮食,可以稳定渡过灾年,所以根本就不动巡幸的心思了。
至于有些网友经常断章取义说的贞元二年唐德宗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用这次漕粮危机来证明唐朝改良运河之后长安仍然会出现饥荒,基本属于不看大背景,抠字眼抠句子叙述历史的典型了。
唐德宗一上台,就杀了唐代宗时期改良运河的功臣刘晏,然后鲁莽削藩。而且他削藩是以藩镇制藩镇,搞得关东大乱,四镇称王,两镇称帝。其中朱泚称帝,还占据了长安,导致了长达近两年奉天之难。
贞元二年漕粮艰难入陕时,虽然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二帝四王之乱还未彻底结束。另一个称帝的李希烈是这一年才被部将所杀。李希烈割据淮西,是运河沿线的割据势力。李希烈死后,运河才重新被打通。
唐德宗二帝四王之乱原本就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至暗时刻,用这段历史去说关中进不来粮,属于典型的断章取义。在全国大乱之时,淮西运河被卡,这个时候别说是迁都洛阳,就是迁都运河更东边的开封,漕粮也照样进不来。因为唐宋元明清都是“奉京师以文化,仰东南之财赋”的政权。江南身处腹地无边患之忧,是真正的生产高地,漕粮主要都是来自于东南。淮河处在中原与东南之间,淮西都称帝了,运河不是被卡,而是被断了。这时候粮食危机是因为战乱,又不是因为地形。极端型洛友经常制造这些混淆视听的说辞,搞得不少一知半解的还信以为真了。可惜懂唐史的一见着地域相关话题就躲,没人正本清源为西安说句公道话。
唐德宗时期削藩失败,关东地区小一半的国土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但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削藩成功,李愬雪夜入蔡州就平定了淮西,基本降服了所有藩镇。虽然唐宪宗死后河朔藩镇又开始搞自治和世袭,但唐德宗时期关东大规模割据的状态已经不存在了,河朔藩镇也至少还尊奉唐廷。此后中唐一直比较稳定。
唐宣宗,光复河陇之后,西北漕粮需求又暴涨,唐宣宗最后一次改良漕运时还年入长安120万石。唐朝不是宋明那样动辄六七十万京师禁军的强干弱枝军力部署,唐朝京师禁军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万。多数时候是十万出头,这个运额的漕粮在刘晏将漕船损耗降至接近为零的唐朝已经够用了。这种年运额也足以让长安渡过灾年。即使到了实质性丧权的唐昭宗时期,在朱温进入关中前的十几年,朝廷动不动还能在禁军折损殆尽后迅速爆兵数万乃至十万,只不过唐廷由于自己的内部制度机器老化问题已经病入膏肓,一次次迅速爆兵,一次次打水漂。
中晚唐虽然跌跌撞撞,但能熬一个半世纪,逼近东汉定都洛阳的165年和北宋的167年,难道只是运气好,在遍地是雷的雷区没踩爆吗?
说到长洛历史话题时,历史如果有主次,但好像地域平等这个政治正确要求讨论历史就不能说主次...我也已经很克制了,但极端型洛友还是觉得不满意,觉得我不能下降到他那个宣传口号和满嘴人身攻击的层次、水平和素质去响应他的观点...我只能说,我真滑不下去,不好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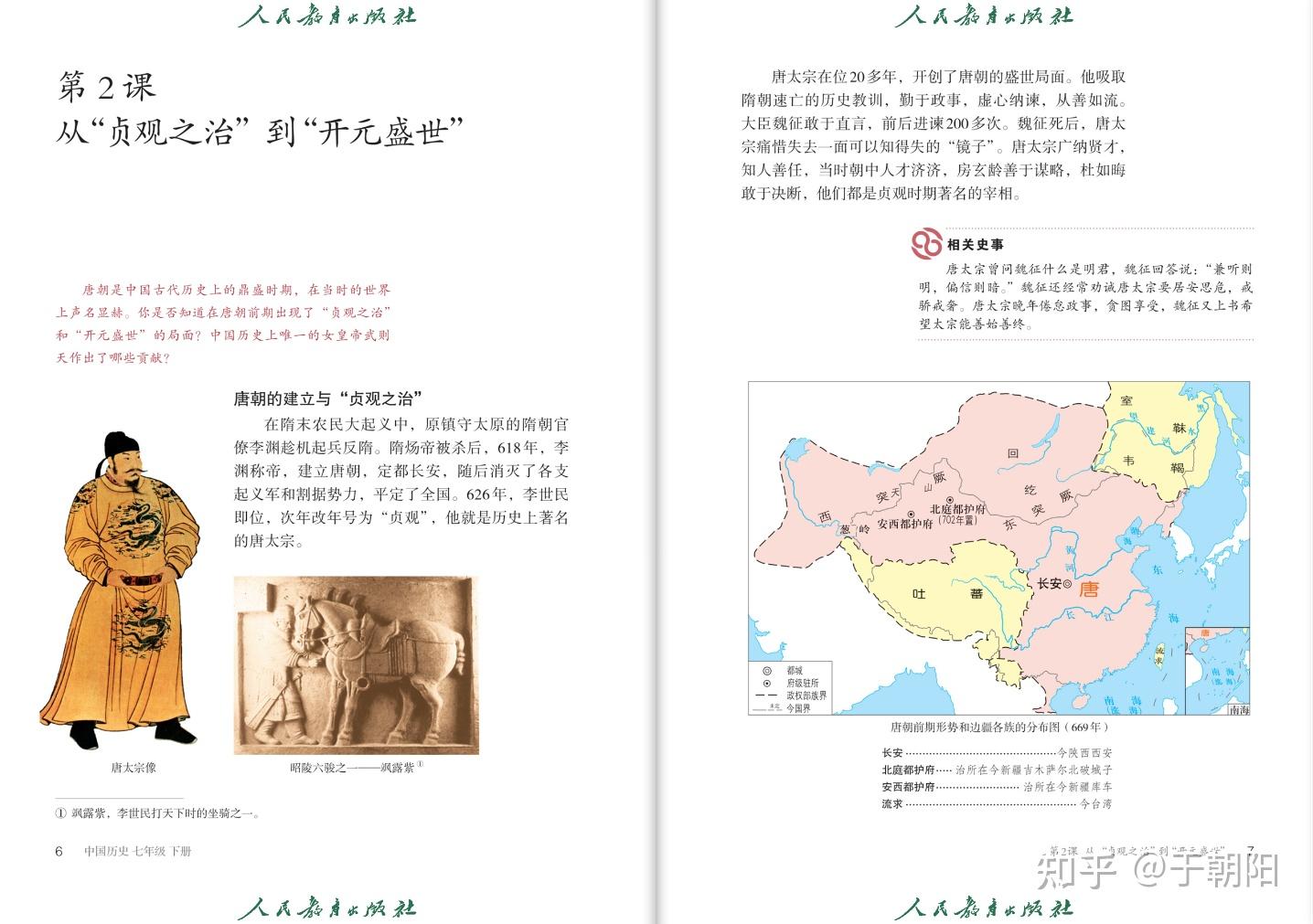
教科书,另外引一个
的国家博物馆的图:长安只是西宅,不是唐首都。我错了,你对对了。唐朝首都在洛阳,长安只是陪都。高兴就好,高兴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