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和《芭比》两部电影,在最近的社交舆论场上,产生了一幅幅魔幻图景,引发了不少了口水战,在人们享受口舌快感的同时,我们也是时候来分析一下里面的玄妙了。
这两部电影,一部是东方古典主义的奇幻巨作,一部是西方资本乐园的反思拷问,一部以男性为主要阵容,一部以女性为主要设定,一部在“弑父”与“换爹”的剧情中展开,一部将父权凝视表现到极点。
于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同样的时间点,当它们一起上映时,属于男性和女性两个身份的城市小布尔乔亚们,在看完电影后,有的神经末梢紧张,有的PTSD爆发,有的按捺不住想要一吐为快。

那么,大家为什么要吵?又在吵什么呢?
贯穿《封神》全片的,有一个关于“弑父”的主题,这在西方文化中俯仰皆是,被借过来使用了。
在电影中,戏份最多的“四大质子”,从小被作为人质,押送到朝歌纣王身边,于是他们就拥有了两个父亲,一个是他们血缘关系上的亲生父亲,分别是东南西北割据一方的诸侯,另一个是从小教导他们的精神父亲,给他们官职,为他们洗脑的纣王殷寿。

当几个亲生父亲要发动叛乱时,四个发誓要效忠大商的质子们,此时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把亲生父亲做掉,还是把剑插进纣王胸口。
在平均三分钟一句的“父亲”“父王”“爹”叫喊中,《封神》被大家喷为“爹味逆天”“爹味全宇宙”,他们说这是亘古不变的文化,信仰爹,怀疑爹,反抗爹,最后成为爹。说这是滑稽的父权制审判,是男凝下的女性剥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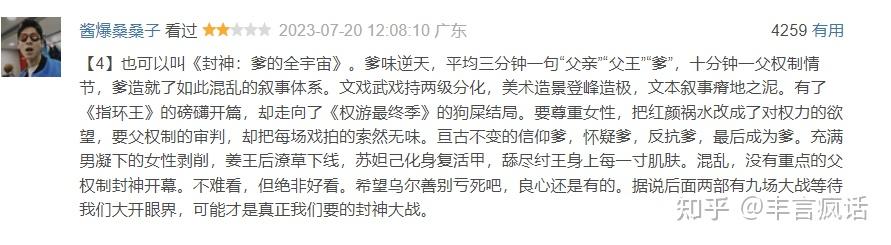
《芭比》的奇幻程度,比《封神》有过之无不及,在一个缤纷的小镇上,这里有总统芭比、医生芭比、法官芭比、作家芭比和美人鱼芭比,她们每天都会举办盛大的派对,她们过得开心又满足。
然而某天怪事降临,洗澡水变冷,早餐变难吃,甚至还发现自己的脚跟竟然贴地,变成扁平足,主角芭比决定跟反派肯前往现实世界。
肯回来后,也把现实世界里关于男性地位的思想带了回来,一股脑灌输给没有抗体的芭比们。主角芭比回来后,则呼吁其它芭比们进行斗争,就这样,芭比们,变成了曾经的肯,反派肯们,又变成了曾经的芭比。
《芭比》当然是更讨女性欢心的,不管是让芭比们狠狠教训那些直男癌的肯,或者是利用男人爹味说教的天性设下陷阱,让肯为了弹吉他、教投资、帮忙修图、解说《教父》这部电影,最终让看似无所不能的男性雄风自取灭亡。

一句“父权制批判”,好像就让《芭比》瞬间升华了。
我以身边统计学的样本,跟认识的知识女性交流了一番,奇怪的是,得到了非常极端的两种评价,一种非常认可里面对女性困境的表达,一种认为这是高浓度的女性爽片,本身也是一种父权凝视,不看也罢。
也难怪,女性内部都有这么大分歧,更何况男女双方了。
其实,不管是《封神》还是《芭比》,这里面有个很可怕的陷阱,重点还不在它们的剧情,而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将身份政治和性别规训,直接明牌。
也就是对立这件事,超出了生活场景,慢慢上升为价值观,甚至是意识形态,最后又反作用于生活,闹出了很多笑话和悲剧。
上一次这么弄的,还是穿婚纱去看明星演唱会,对这场事件的炒作,已经扩散成全民议题,在诡异的营销包装下,支持女友穿婚纱,带女友去看《芭比》,成为了“正常男人的测试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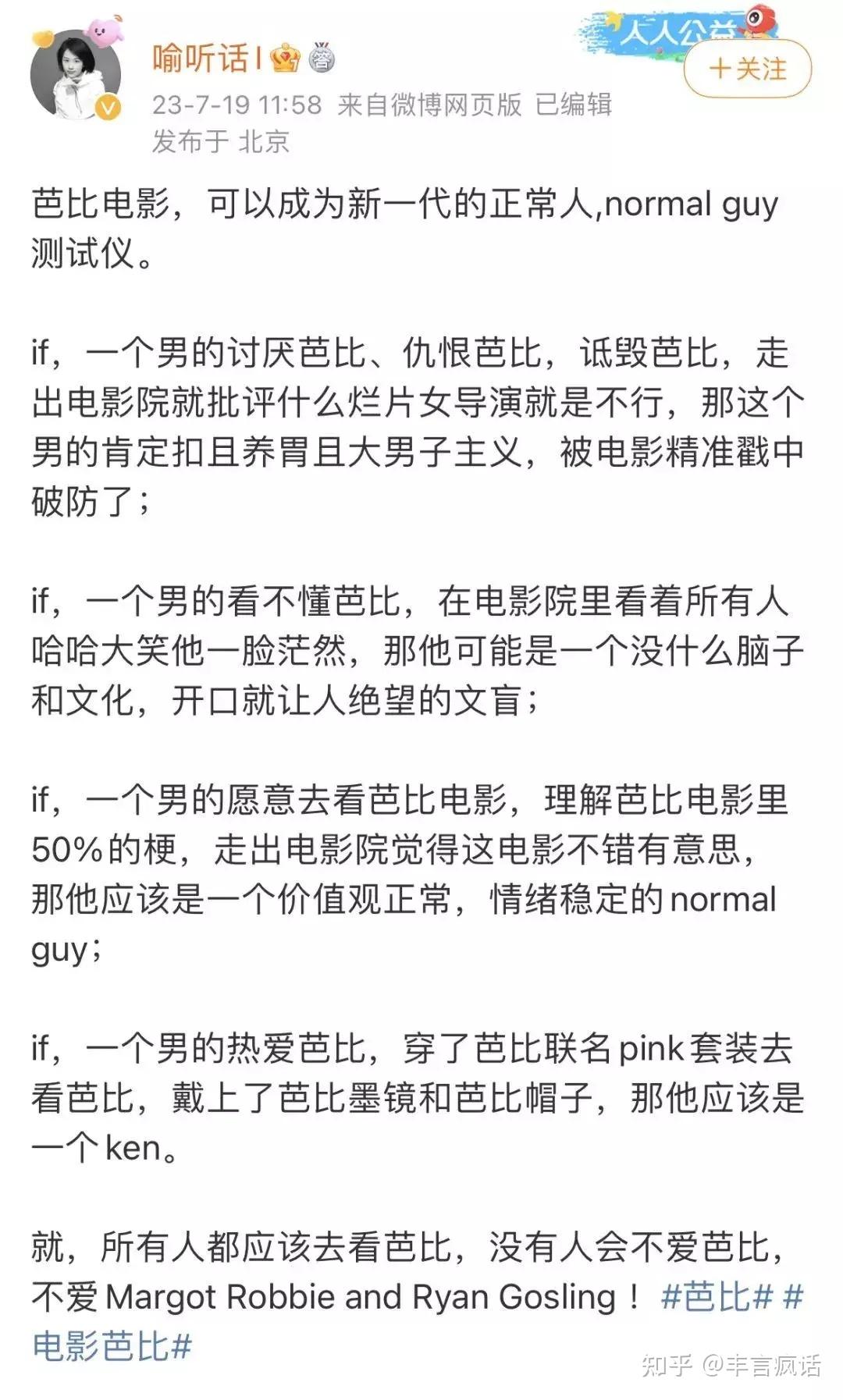
这里面的用心非常阴险和恐怖,因为它将“父权”与“普通男性”直接划上了等号,并进行一场又一场舆论围猎,哪怕波及到最底层最广大那些男性。
说到这里,我猜测已经有人要给我扣帽子了,说我不同情女性的遭遇,无视哪怕在普通阶层中,普通女人也被普通男人压迫的事实。
这恰恰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陷阱。
后现代女性主义,有三个基础命题。
第一,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改进的问题,相反,它是涉及到无限维度的社会根本性问题。现有社会是由父权制所塑造的,而现实中的几乎所有罪恶,都可以归结于父权制度和父权思维的本质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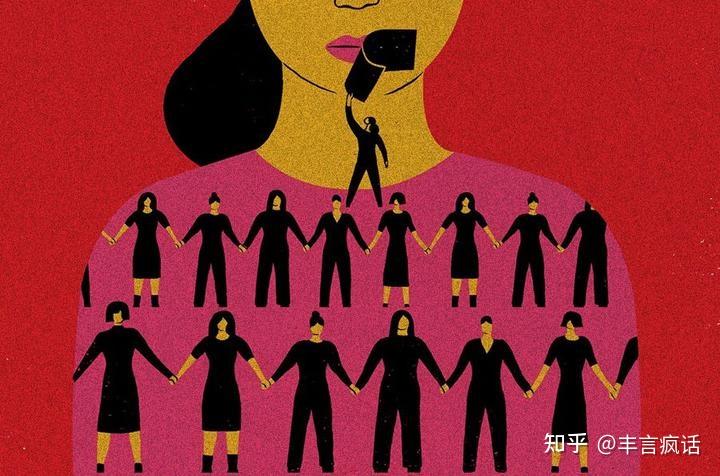
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通过对整个社会构架进行全方位推倒重建,才能解决现存的贫困、不公、战争与压迫等现象。
比如,最典型的一个观点,男人是战争的发动者,没有他们就不会就战争,尽管他们流血牺牲,妇女受到的伤害绝不亚于男人。
可以看到,这里面父权的叙事,已经超过任何的民族、阶级和利益,成为最高原教旨主义。
第二,被压迫群体要自觉行动起来,参与解放运动才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说,只有被压迫者才拥有解放自己的“特殊资格”。
不论男人们有着多么强烈的同情心,多么地体量女性的遭遇,他们都不能在根本上理解女性。最多只能对女性主义事业,起到一点袒护性的支持作用,永远都无法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家和领导者。
同时,由于男性是父权制的主要受益者,由他们主导的社会不可能主动改善女性处境,要实现女性解放,必须彻底推翻父权社会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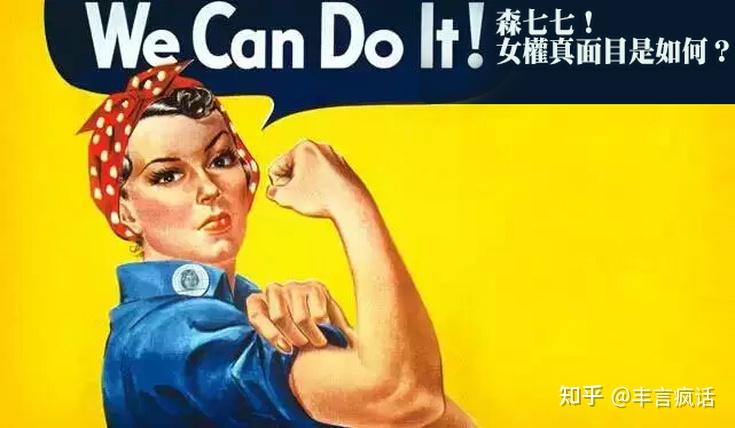
第三,由于现存社会的一切问题根源均在于父权压迫,因此反对父权统治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任何试图对性别议题保持中立,或是不感兴趣的人,都属于助纣为虐,见死不救。任何主要以男性为主的影视作品,不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不声明女性主义意图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助长父权制的气焰。
这三点,可以简单总结为,女性主义永远是正确的,女性主义如果不正确,那就是男权主义造成的,男人是女人的敌人,女性所有的苦难都是男性造成的。
说到这里,不难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设定,在一部分激进的人看来,不支持女朋友穿婚纱看演唱会的,不去阅读女性主义相关作品的,不主动体验生孩子疼痛指数的,都是帮凶,哪怕是沉默者,也属于沉默的帮凶,尽管他们一脸错愕,表情懵逼。
像前段时间,热播的《漫长的季节》,因为王响、龚彪和马德胜,三个男性角色身上的“爹味”,被一顿狂喷,认为他们扮演的父亲和家长角色,是钢铁时代体制的维护者,是傻白甜式的搅屎棍,而所有的灾难都离女性更近。

1994 年,两个科学家保罗·R·格罗斯(Paul R.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把不严肃讨论问题而简单划分立场的人,称为学术左派。
这帮学术混子,不在于他们拿出了什么响当当的证据,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恬不知耻地强调道德优越感。
如果你反对女性主义,那么你就是维护旧有的男权世界罪人;如果你对生态环保的花言巧语持有异议,那么你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污染者的代言人。
其实,整个西方世界目前就陷入了这种怪圈,由白左竖大旗,互分阵营,非黑即白,成天玩政治正确,大打出手,斗个你死我活。
而对父权制的批判,也被打上了某某主义,当代社会,就是一个“主义秀场”,女性们争着抢着穿,谁一穿上这件“主义”的礼服,不但占据了互联网话语权的高地,还神功附体、刀枪不入、天然正确、风华绝代起来,这就是网络义和团。

在这面时髦大旗下,聚集着着各种主义理论家、流氓无产者、曝隐爱好者、PTSD患者、受害妄想症者、名利饥渴症人士......这些激进的某某主义者,并不想真正去解决社会现实,更喜欢互相串联,集体群殴,享受口舌快感和唾沫狂欢。
在后现代主义和这种魔幻现实下,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确实比过去更强了,她们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作为一个主体,不能只是个宾语,仅仅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强调自我,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语言符号本身便是一个父权话语体系,女性主义陷入一个悖论,她们在用父权符号反对父权话语。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她们若要获得绝对胜利,就必须启动一套女性话语体系,以女性符号完全代替父权符号,让整个社会体系服从女性律条。
比如,不叫“男女”,那就得叫“女男”,孩子不跟父亲姓,就一定要跟母亲姓,结婚生子是对女性的剥夺和牺牲,不结婚生子就是唯一的正确和解放。
由于后现代主义女性理论,对一切现有的性别关系持有怀疑态度,全部归咎于男性的驯化,他们为了创造话语而不惜一切,要么创造假想敌,要么自我制造恐怖阴影,四处挥拳。
在强势话语的掩盖下,在各路女武神的征伐杀戮下,被波及的无辜男性,要么缄口不言,保命要紧,要么理性辩论,然后被唾沫星子埋没。
斗争扩大后,这样就会使原本支持平权的男性,放弃幻想,同样加入战斗,在不久的将来,就是真的是雷声隐隐,风暴来临了。
恐怕以后类似的电影上映时,只会掀起更大的舆论风浪,甚至我不惮地猜想,可能以后大家去看电影时,真的得男女分座了。
参考资料:
《<高级迷信>:反对后现代与激进女权主义的理性手册》Maverick
《在话语群殴的口舌快感中,激进女权成了当代的义和团》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