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句话有一个同位语,叫做【妈妈给我说,要和比自己成绩更好的人交朋友】。
这就是单向度的交友模式,因为倘若别人也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和自己交友的话,那就变成了【能和我交朋友的人,都是不如我的人】。
我打小就发现了这句话的漏洞,但这不能怪这句话不对,我小时候本来就很调皮,被孤立霸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其实在超级英雄系列作品中也有相似的逻辑,那就是【超级英雄】应该是全能的,而不应该是【只在某个地方有特质】。
因为在这个逻辑下,超级英雄=神明=万能。
在一个零和游戏里,人们看似是可以争取到【最高位】的金字塔者,但人总是会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可以是天命,可以是时代,甚至还可以是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东西——死亡。
回到这个社交话题来说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位居【最优秀】位的人可以【剥夺】他人的价值——这是神才能做的事——所以才会在【位置】上给其他人带来持续的压迫感。不过这个【最优秀】者最后也不得不面对一件事,那就是他必然有朝一日会不再强大,会一步步衰老迈入死亡。
所以真正的社交焦虑在哪里?在那个最优秀者那里。因为人最后一定会走向死亡,所以再如何靠近神,也只是僭神者而已。

我不够优秀,当然在【别人】眼里就没有价值——这当然是对的,何止是没有价值,已经可以当另一种物种来看待了。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人被当做【资源】,就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压倒了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的结果。
当然价值理性不是那种“价值”,说的不是最后被计算出来的结果,而是在完成一件事中间形成的体验,是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就好像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所说的那样,艺术品没有形成之后进入与观众的品鉴过程,而是在与观众的参与和传递中才得以完成,这不是评析,而是体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超人”的印象从简单的力量大的全能状态,变成了只有某个领域的尖端状态的印象了呢?后来又变成了只要特别就可以呢——甚至好多能力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比如
那是因为从九零年代到零零年代,对这些超能者的想象力发生了变化。
从潜意识上说,任何生活在当下的(尤其是网络文化和漫画文化侵染下成长)年轻人来说,想到超人,都会下意识想到美国超级英雄系列里的那个来自外星的氪星人超人,然后才会开始进行其他思路的探讨,这就是文化带来了对想象力的重建。
这种重建就是基特勒所说的媒介(形象)在无形中改造了人们的思想。
但是这种【强者大逃杀】的逻辑随着决断主义的失效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开始向【弱者大逃杀】发展了。
宇野常宽就曾经说过,时代变了,大人!
从“晋级赛”(tournament)到“卡牌游戏”
他们并不是挑战比自己处于上位的强者,而是寻找与自己一样的弱者(玩家)的弱点,趁虚而入,依赖自己的“一艺”在残酷的生存游戏中为了活下去而战斗,而他们自己也不过是无数玩家中的一员。
可以说,我们如今生存其中的世界也是如此,并非晋级赛而是卡牌游戏,并非“金字塔型”而是“大逃杀型”。这一变化完全符合大叙事凋零、小叙事林立的后现代状况。世界的变化,切实地影响着我们的想象力与世界观。
如果说【强者大逃杀】的本质是 在有限人数中存活下最优秀的那个,那么【弱者大逃杀】的本质就是 在有限人数中存活下最多数的那些。
而只要存活下来,也就意味着不需要一直获胜,哪怕失败也没关系,因为可以联合与自己力量迥异的其他弱者即可好好生存。
我们这些弱者的本质,不是为了展开【互害】,无论是底层还是中、高层,而是通过与其他不够全能的朋友联合起来的方式,反抗整个【游戏机制】——以及整个【社交机制标准】。

说句不好听的,这套【不够优秀就没有价值】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认为有用的话,那必然就是错误的理论——如果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下,人们必须快节奏跟上步伐,要不然就会被抛弃;那回到慢速生活的时代,人们又必须要展开存量争夺,要不然又会被蚕食——那么就不是时代发展快慢的问题了,而是标准设置的问题。
就像李雪琴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在社交上都会精于计算的话,那还有什么不会计算呢”?
更进一步的说,拥有全能的超人的想象,以及“假如未来”是一种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对当下的生活状况处于无视的状态。而只有某领域的个别超能力的想象,是对现在的共存想象,不愿意未来以一种审判的姿态降临。
我来说点自己的故事吧,做人第一是善良,第二是诚实,第三就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最我来说,这句话最有效的时候就是在学校里,因为学校并不是【最单纯】的空间,而是有着【最可见标准】的空间,那就是成绩排行榜,它最后会以一种末日审判的方式把所有学习的过程都做出最终宣判,那就是高考。
所以,在初高中期间,我认为这句话就是金科玉律。
后来进入大学之后,这句话的价值轰然倒塌。
一则是标准的多元化。虽然大学期间也会看成绩排名,对考研保送的学生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还有其他标准,比如考公考编的勤奋程度、做学生干部的参与程度、热爱生活的自媒体记录、兴趣爱好的共同体们......如此种种,肯定不只是【成绩】能涵盖的。
二则这句话也有问题。我们以为的“别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优秀的标准是成绩排行榜,所以没有价值的发出者只有【成绩单】。
再后来进入了社会,发现不再是要优秀了,而是要形成系统化。
社会组织结构要求人们社交的,就不在是优秀了,而是变成了成系统的生态位。能够“物尽其用”的出现。
于是在社会家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应该认识这样几个朋友:当医生的、做老师的、在媒体的、开饭店的、在体制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人】如果啥都不是,凭什么应该成为别人的朋友呢?
是不是就又回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焦虑中去了呢?所以用句俗语来说,你有没有价值,是否值得被社交,根本就不在于你是否优秀,而在于你是否有统战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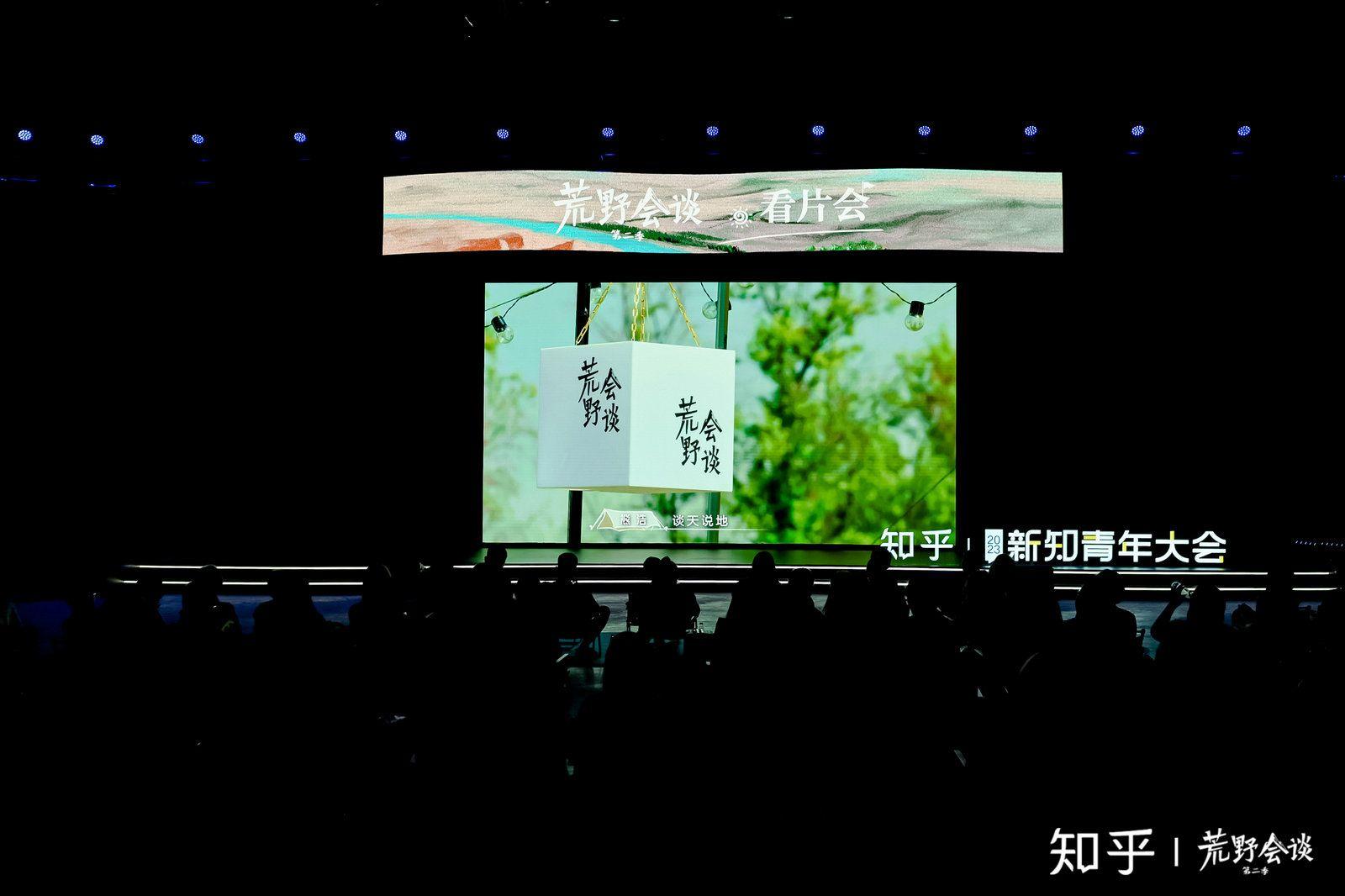
所以说,我们应该暂停下来,进行一次与city walk 相对应的 wild talk(荒野会谈)。
不用去现实生活里解决问题,而是一次闲谈中抛出问题,不用将自己作为符码去天平上权衡利弊,而是抽离出来观察这个世界,在摄像头的视野下交流自己。
说起来在看片会的时候,席瑞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认为非常有道理,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不是去照顾别人,不是去让别人照顾自己,而是真切的熨帖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用去管什么“查询自己的精神状态”,哪怕即便是短暂地享受其中,去反思一两个和现实毫无关系的思想实验问题,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