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
和 稍微商榷一下,这种史观来自法国或者瑞士社会党的可能性其实都不大。“斐迪南军国主义者”论应该一方面源自中国自身对一战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多少受到中国跟南斯拉夫蜜月的影响。列宁对一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列宁的这一论断,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定性一战性质起了很大影响。相比原本身为列强的俄国,原本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对塞尔维亚有更大的共情(当然塞尔维亚问题的真相其实没那么单纯),对侵略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评价也更差,甚至会自觉不自觉把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关系类比成中日关系。因而将被击毙的斐迪南大公直指为“军国主义者”也很正常,这并不需要什么法国因素或瑞士因素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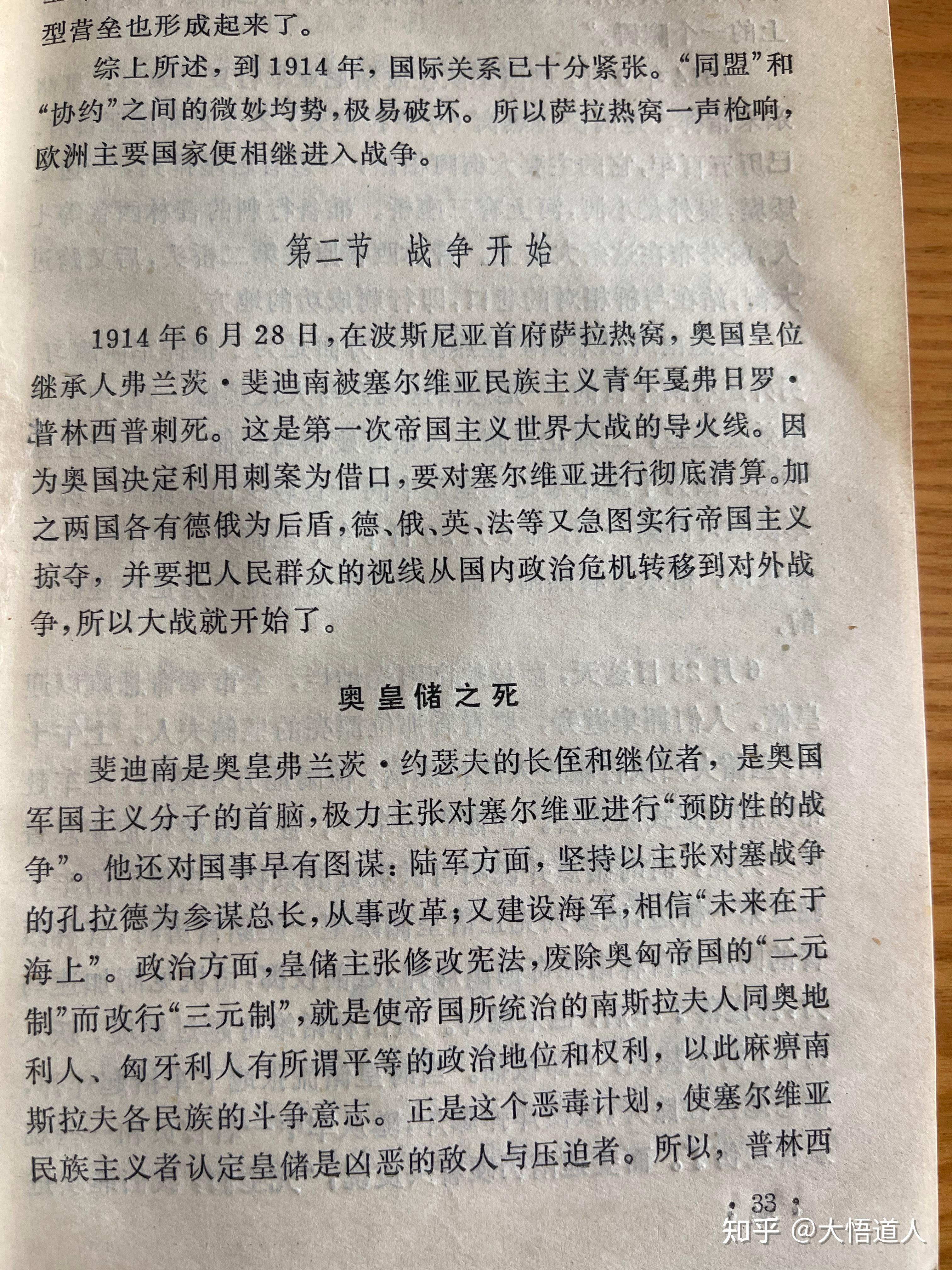
在1973年(当时中国和南斯拉夫尚未进入蜜月)版的一战简介中,强调斐迪南是“军国主义分子的首脑”,措辞上似乎跟“军国主义者”稍有差别。这本书对普林西普也未见有赞颂之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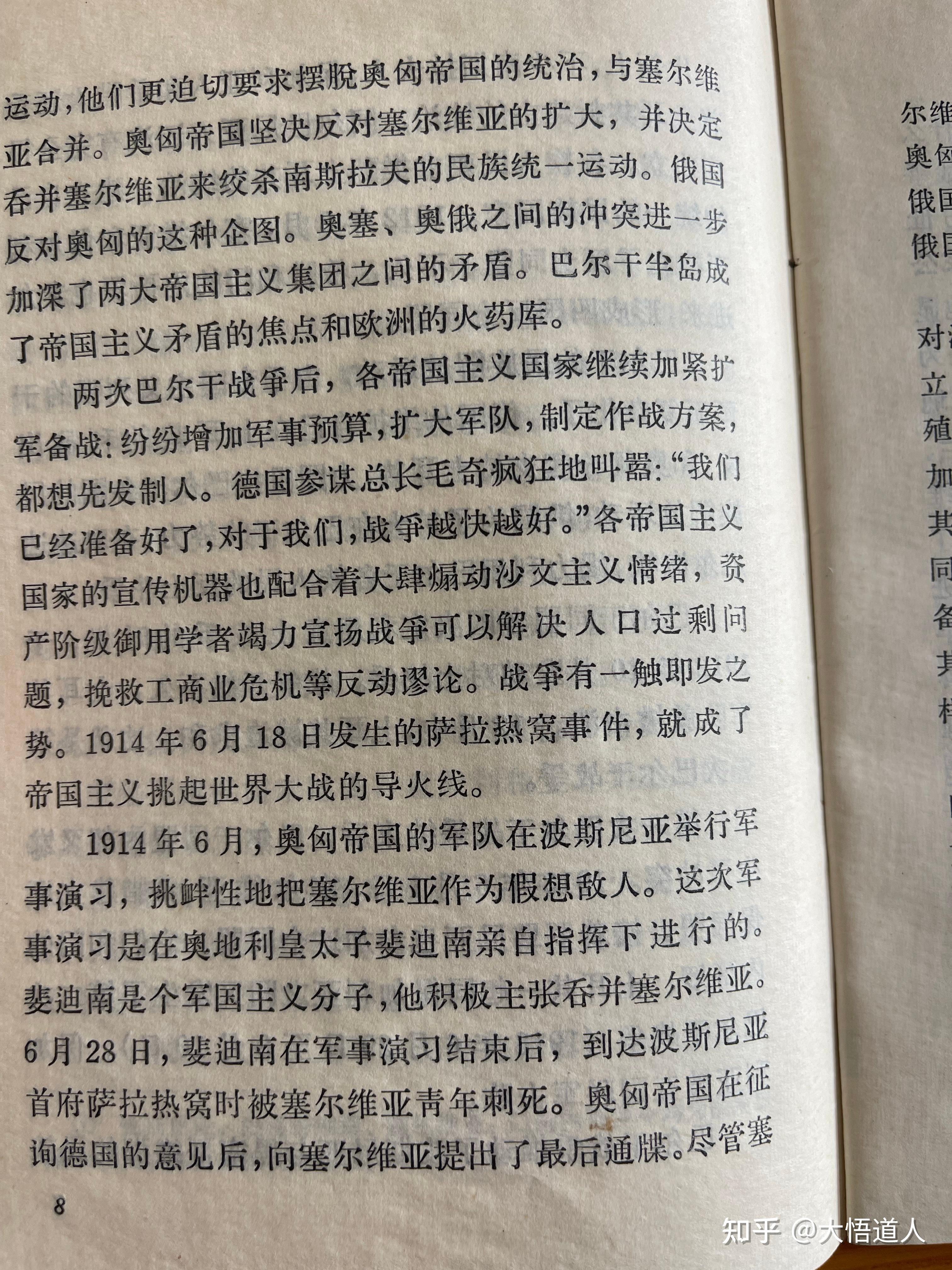
1977年铁托访华,次年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中国和南斯拉夫进入蜜月期,作为友好国家,中国自然对一战时的南斯拉夫各民族更加有好感,对压迫各民族的奥匈帝国更加痛恨。于是1979年所出版的一战史,就明确把斐迪南视作“军国主义分子”,并赞颂普林西普是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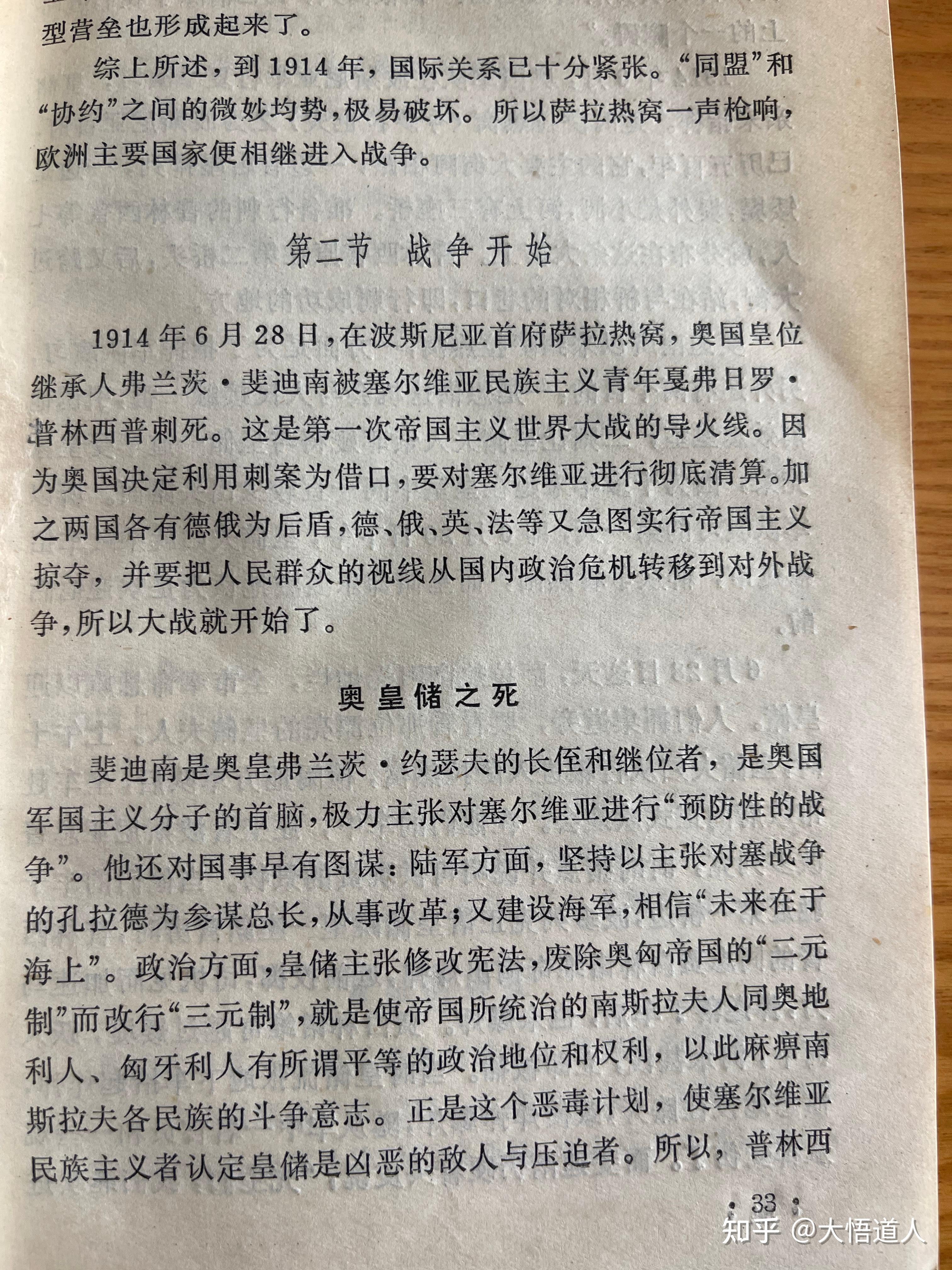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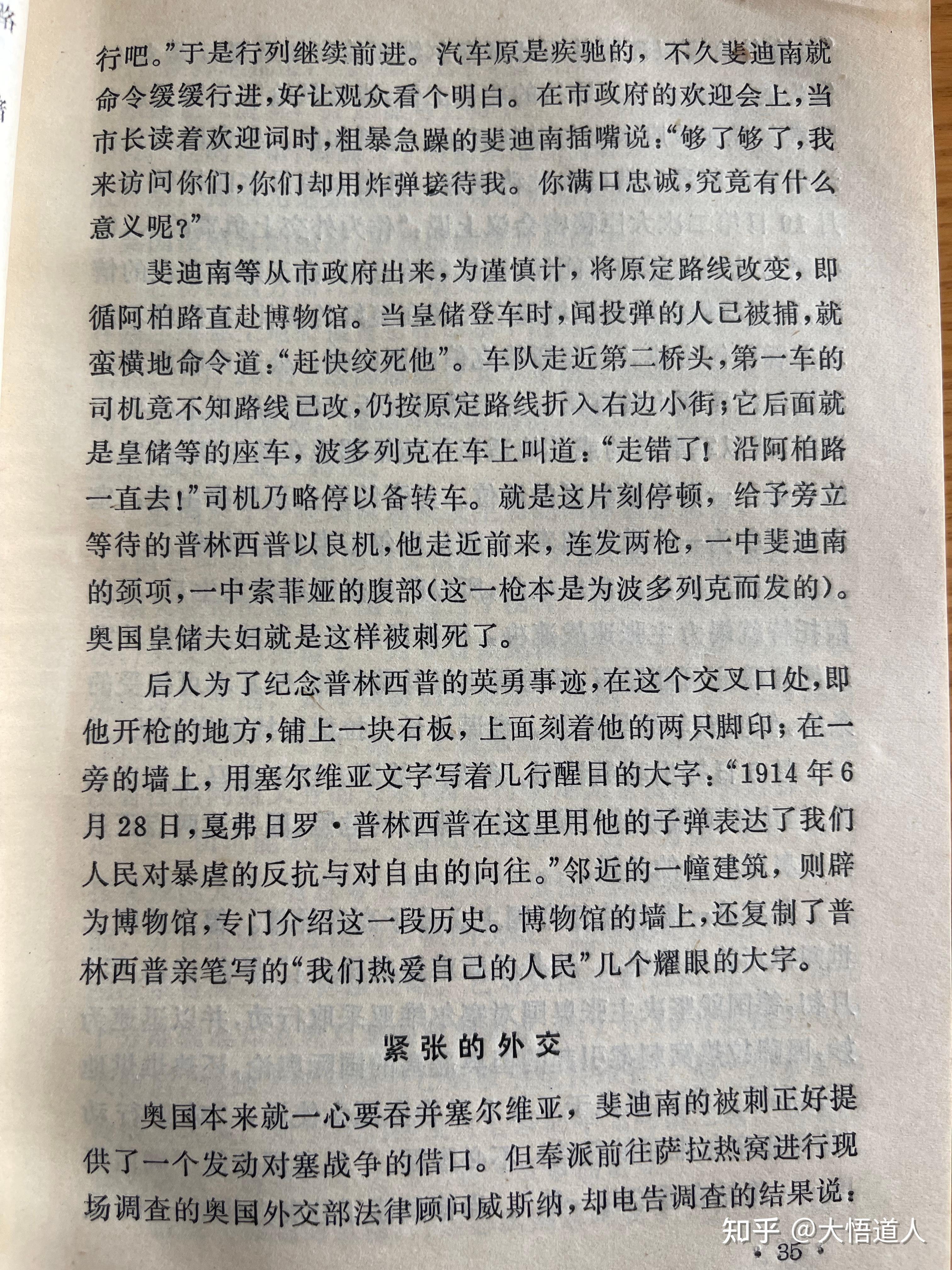
在中南蜜月期,中国对一战中塞尔维亚的遭遇也比文革时期更加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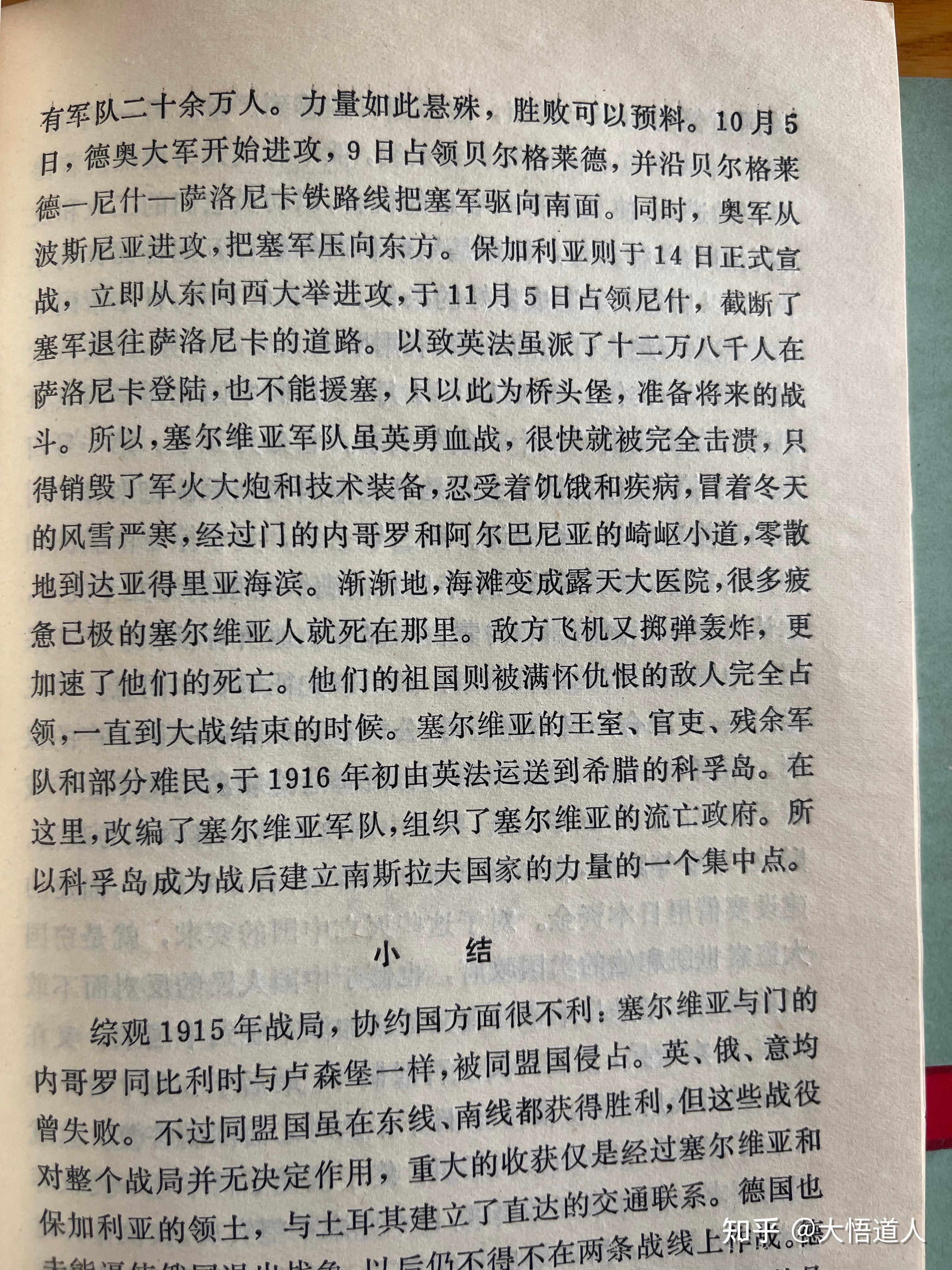
当然如
指出的,苏联的世界史教科书对斐迪南本人并没有怎么抨击,甚至普林西普也是“恐怖分子”而非“爱国英雄”,不过这一点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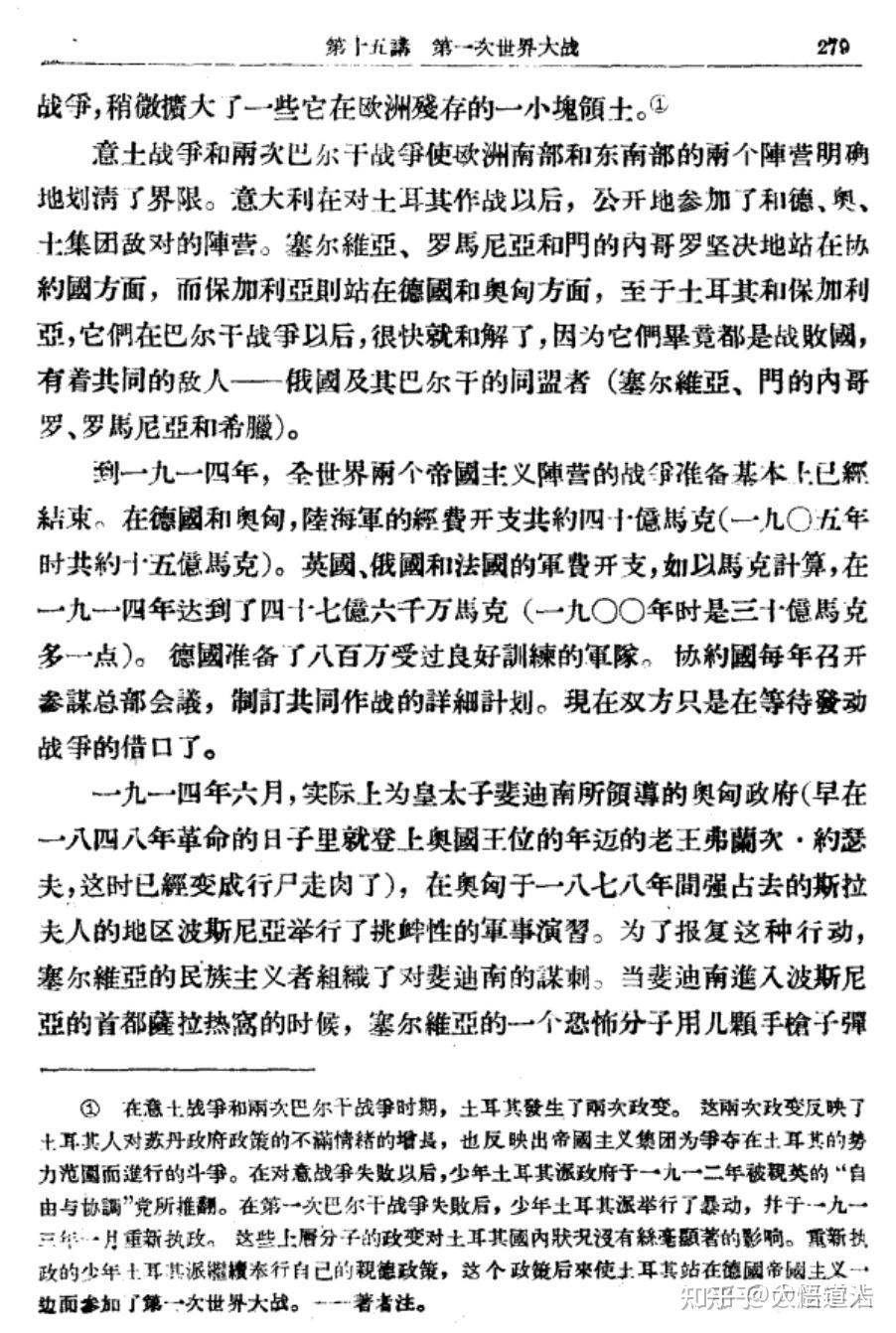
这部书在中国出版于1956年,写成的时间肯定更早,而苏联跟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是1955年,所以苏联学者把“敌国”的人描述为“恐怖分子”也算情理之中。
编辑于 2023-02-12 16:26・IP 属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