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郭老锐评胡博士。
巫觋已经不是我们再去拜求的时候,就是在近代资本制度下新起的骗钱的医生,我们也应该要联结成一个拒疗同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
“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
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
……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1]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
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但他在术语的使用上有很大的错误。发见仰韶辛店等时期的安特生(J. G. Anderson)疑商代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是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这时候已经有铜器的使用。(安特生在甘肃的收获中也曾发现了一个小铜扣。)考古学上一般是称为金石并用时代,胡适漫然地引为石器时代,并于“石器时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时代”,这是大谬。盖新石器时代为期至长(单言石器时代更无庸说),早的如象埃及开幕于公元前一万二千年,中间的绵延有六千年。其他欧美各国,大抵均开幕较迟,而绵延却约略相等。中国的地质学上的时代,在目前科学的发掘方在萌芽之时,自然谁也说不出它的定限,然而殷代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即金石并用时代,却是可以断言的。以周、秦为“铜器时代”亦是错误。在考古学上铜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判然有别。铜器时代是新时期时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并用时代的另一种说法。青铜器时代则是更高级的文化,周、秦确已是青铜器时代,照现在所有的古器物学上的知识说来,连殷代末年都应该包括在里面。胡适泛泛地以石器时代概括商代,以铜器时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来虽仅是一二字之差,正是前人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胡适又说:“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以上见原书第九八页)
这个态度比较矜慎,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个问题。
胡适的见解,比起一般旧人来,是有些皮毛上的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2]
——《夏禹的问题》,1930
还有一件大公案、就是胡博士《说儒》的是非。郭老的见解主要集中于《借问胡適》(1937,後改名《驳〈说儒〉》收入《青铜时代》)、《论儒家的发生》(1942,後收入《史学论集》)、读者可自查、俄且摘引驳胡特有力者。
《借问》云、
胡适的 《说儒》,初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后收入《论学近著》。他说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 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他有一段文章,把孔子和耶稣对比,我且把它抄在下面: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以赛亚书》五五章四节),‘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之中得保全的人民能归回这还是小事——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推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的尽头’(同书四九章六节)。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后来他被拘捕了,罗马帝国的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 王啊!’戏弄过了,他们带他出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归回’的梦想,就这样吹散了。但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死了又‘复活’了:‘好象一粒芥菜子,这原是种子里最小的,等到长大起来,却比各样菜都大,且成了一株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真成了‘外邦人的光,直到地的尽头’。
孔子的故事也很象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期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大囏是承,肇域彼四海’。后来这个希望渐渐形成了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引起了宋襄公复兴殷商的野心。这一次民族复兴的运动失败之后,那个伟大的民族仍旧把他们的希望继续寄托在一个将兴的圣王身上。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就是和他不同族的鲁国统治阶级里,也有人承认那个圣人将兴的预言要应在这个人身上。和他接近的人,仰望他如同仰望日月一样,相信他若得着机会,他一定能‘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他自己也明白人们对他的一望,也以泰山梁木自待,自信‘天生德于予’,自许要做文王周公的功业。到他临死时,他还做梦‘坐莫于两楹之间’。他抱着‘天下其孰能宗予’的遗憾死了,但他死了也复活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他的说法,基本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对比上。这是很成问题的。当然,为了要建立这个对比,他也有他的一些根据。我们现在就请来追究他的根据。
……
胡适似乎很相信《周易》,《说儒》里面屡屡引到它。最有趣味的是他根据章太炎把《需》卦的那些卦爻辞来讲儒,他说那儿所刻画的是孔子以前的柔懦而图口腹的儒者。孔子的出现是把这种儒道改革了的。有趣是有趣,可惜牵强得太不近情理,记得已经由江绍原把他驳斥了。但他除《需》卦而外也说到了其它,你看他说: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巽》等等教人柔逊的卦爻辞,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论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
这儿的大前提中也把《周易》的《谦》、《损》、《坎》、《巽》等卦包含着。《周易》里面也有《乾》、《大壮》、《晋》、《益》、《革》、《震》等等积极的卦,为何落了选,都暂且不提。其实要把《周易》来做论据,还有一个先决问题横亘着的,那便是《周易》的制作时代了。这层胡适也是见到了的,你看他说“《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但回头又下出一个“推测”说“《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之中”,而断定作者“是殷人”。这个“推测”和断定,连边际也没有触到。关于这,我在三年前已经用日本文写过一篇《周易之制作时代》。发表在日本的《思想》杂志上(一九三五年四月)。那文章早就由我自己译成中文寄回国去,大约不久就可以问世了吧。
……
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殷灭于周,其在中国北部的遗民在周人统制之下化为了奴隶。在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动摇了起来,接着便有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而儒开其先。这是正确的史实。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而且不断地在证明着。《说儒》的出发点本就在这儿,虽然胡适对于我未有片言只字的提及。但是从这儿机械式的抽绎出这样一个观念:儒是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得到孔子这位大圣人才把它“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更从而牵强附会地去找寻些莫须有的根据;这却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种的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主张实用主义的胡适,在这儿透露了他的本质。[3]
《发生》云、
胡适的《说儒》,以“三年之丧”、《易经》的需卦、《正考父鼎铭》、《商颂·玄鸟》四点为根据,证明儒为殷之宗教,充分带有奴隶根性而柔顺,迨孔子出世,始改为刚毅的宗教。今天从所引的四大证据来研究,“三年之丧”是孔子创造的,《易经》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正考父的谦恭,不能作为奴隶解释,他是殷之顽民宋国的贵族,并不是周朝的奴隶,而且正考父的《鼎铭》是后人假造的,孟僖子的故事,也是假的,《玄鸟》诗,不能作预言解释。四根大台柱,不能成立,对儒家的看法,就是根本错误,只好垮台。[4]
而以後世重审此案、尤小立教授有过综述。
但俄以为尤教授实有有袒胡之嫌、如、
1975年,徐中舒发表了《甲骨文中所见的儒》[39]。此文不仅运用甲骨文数据支持了“职业说”,且证实了胡适“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论点的正确,这也等于否定了郭沫若驳胡适时所说的“儒是西周时期邹鲁缙绅之士”。尽管因年代特殊,未提胡适及其《说儒》,但徐文用甲骨文中的新证据,充分肯定了《说儒》的学术价值。
案、依徐说、固然郭开贞先生主张儒家起于周代是不对、可也并不是「证实了胡适“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论点的正确」。因为胡氏「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云者並不是说商代已有了《儒》、而是说商人遗民在商朝後演变成了《儒》。所以徐说恰恰也否定了胡说。这是只要看过《说儒》通篇、就很清楚的事。故而疑尤教授实未认真通读文献。
《说儒》云、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
大概周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国学论丛》一卷一号,页一一一。)此说似甚有理。“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博斯年先生疑心“儒”是古代一个阶级的类名,亡国之后始沦为寒士,渐渐得着柔懦的意义。此说亦有理,但此时尚未有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儒”为古阶级。)
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盘剥、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了。
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职务。……[5]
徐氏读商代卜词「需」为《儒》、并指出「丘儒」等、准此、不但商代已有这个专门的《教士》阶层、而且已名为《儒》、这和胡氏前述《亡国为奴、养成柔懦、名为〈儒〉》云云不是全相抵触的吗?
“职业说”也不是胡、郭分歧的关键。徐氏以商儒为相礼之士、郭氏也未以为古儒不是相士、只是否认《术士》说、以为非秦以前古义。
最後、徐氏以《儒》得名于《濡》即浴身的仪式、也和胡氏不同、尤教授在《关于“儒”的字义》一节全不提及、倒是责怪後学、
郭伟川写有《古“儒”新说——胡适之与傅斯年二先生论说》[52]一文,反对胡适解“儒”为“柔弱”,……不过,郭文大多局限于今人的观念,对胡、傅之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影响了其结论的客观。
这是何等的客观呢!
不过、徐先生此篇亦未必能为定论。这里只是澄清学术史上的一案。
尤教授最精彩则莫如、
《说儒》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模拟基督教的“悬记”被多数论者讽为“无稽之谈”,这种笼统地拒斥,实际上阻碍了后人对《说儒》的深入理解。
童炜钢《胡适的“儒学”观》[74]是少数以研究的态度解读《说儒》中宗教问题的论文。他认为,耶稣作为政治兼宗教领袖,本来就是传道和从事秘密串连活动的“弥塞亚”。这一与孔子的相似处也是胡适构思《说儒》的灵感之一。可惜作者没有进一步地讨论。
林正三从胡适文化交流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又译选择主义)原则上理解胡适与基督教的关系。他发现,胡适用基督教的“弥赛亚”作为“支持成分”,再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结构《说儒》。胡适“以宗教观念为钥匙,打开无数的古锁,灵感泉涌,新意迭出,……似乎期待《说儒》将造成另一波的‘史学革命’。”[75]但作者未能发见《说儒》文化上的寄托。
俄则以为、《文化学》的解说对自负《攷拠癖》、申张乾隆—嘉庆洖学科学的胡適博士而言是批评而不是褒扬。
这却揭出胡博士自身的二分、一个实证主义的国学批判家、一个《整理国故》的文化名流、余英时辈谓之《知识人》者。前一个胡適是引领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的胡適。可惜《但开风气不为师》、其实佗在学问一途也並非本色当行、早有许多学者指出其瑕、故而不够资格为师的。后一个胡適是翼赞蒋反革命集团、弃华人、华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代表华国的驻外大使)之自尊于不顾、而摆弄 Sinoloy 即 orientalist China Study 的反动的胡適。胡適先生垂世的名言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可是佗本人的《问题》实在《硏究》未通、只有早年主张的资产阶级启蒙这一《主义》是《谈》得最有益的。这也真是史的绝大讽刺了。
尤教授还援引了不少杨向奎先生的评述、为胡博士张本。可是以俄读者、杨先生也指出的胡氏此篇的相当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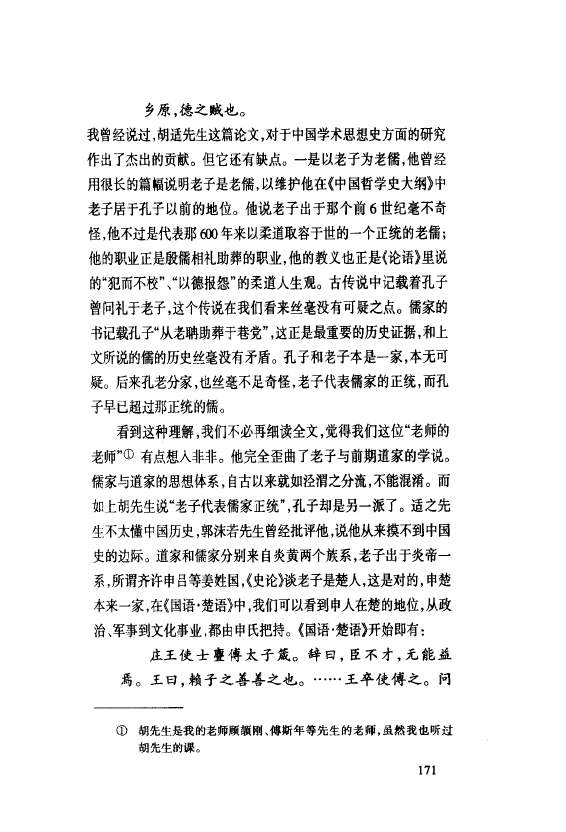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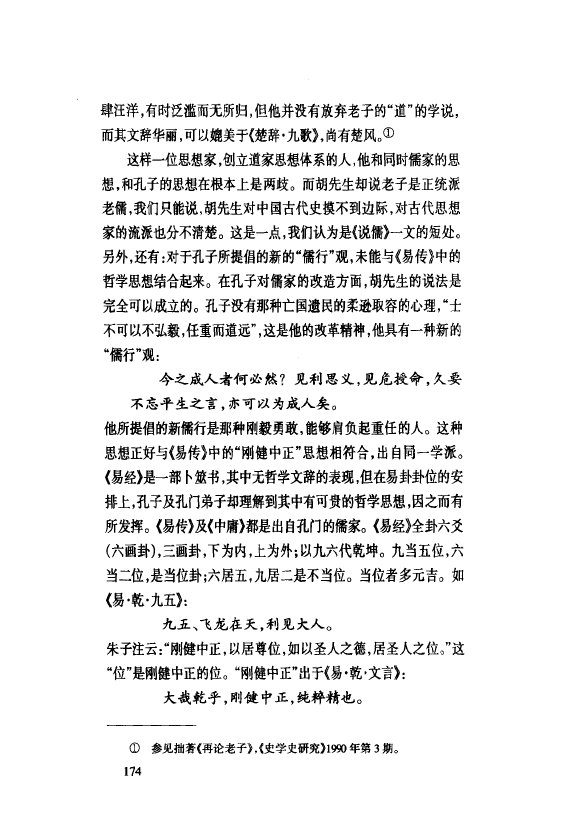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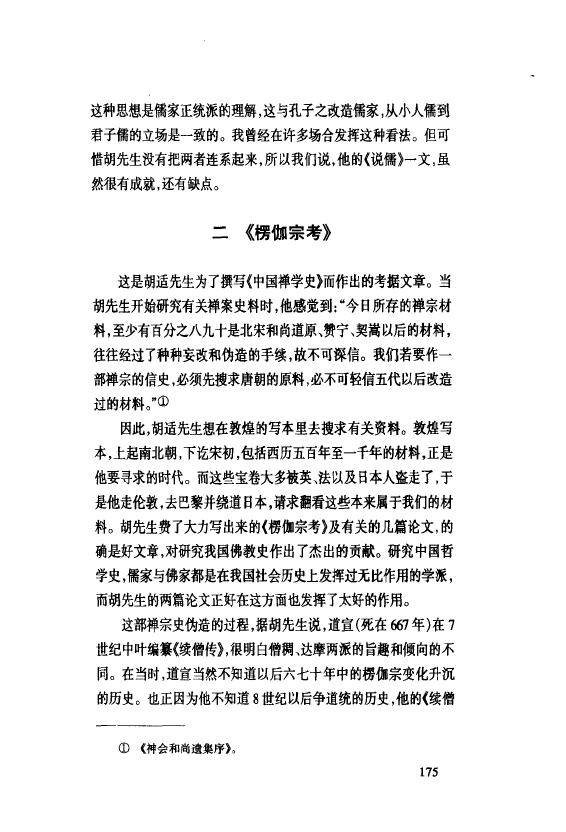
总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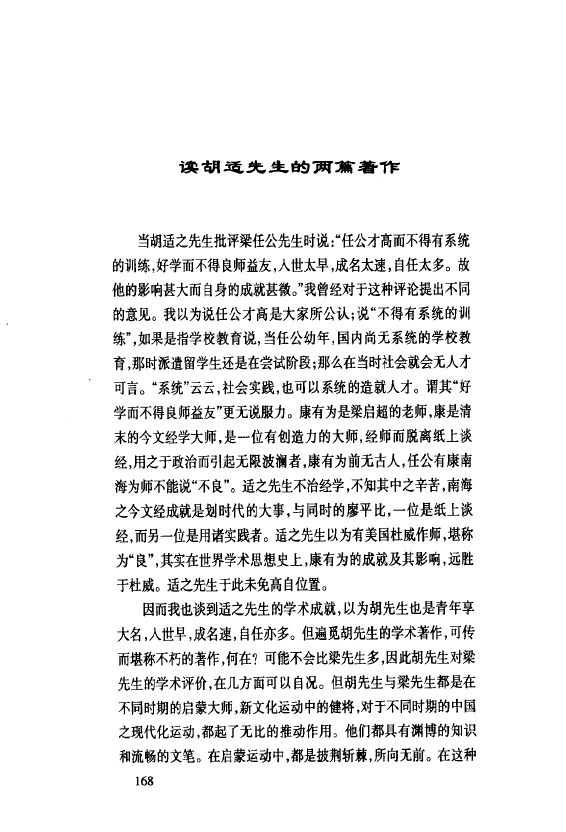
但遍览胡先生的学术著作,可传而堪称不朽的学术著作,何在?
对企图将胡博士装点为学术大师的评家来说、俄以为杨先生的问是很可悲的。
此外、杨先生还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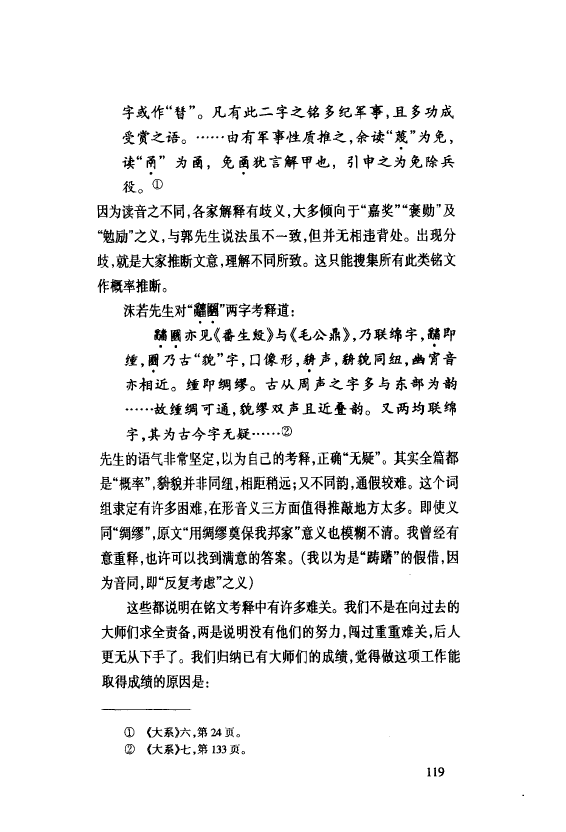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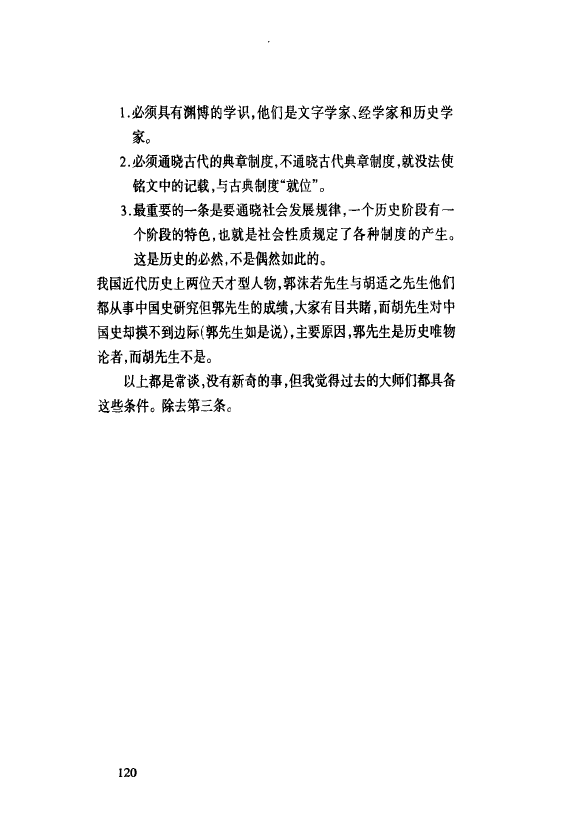
杨先生是个很率直的人、所以佗谈到别人、极高与极低的判词可能同时出现。这里、佗承认胡博士为《天才》、但同时也认可郭说、以为胡博士在史学上是不够格的。俄以为若仔细体会这意思、佗这个反差的判词和俄前言《胡適的二分》是一致的。
以上着重说到郭先生、徐先生、杨先生、三氏彼此虽有分歧、却是近世俄最推重的三位古史专家、所以相对熟悉些。胡適先生则不在其列。这是因为俄看出佗们的为学态度截然不同。
参考
- ^文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校订过,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https://zhuanlan.zhihu.com/p/184901849
- ^文据《全集》历史编卷一校订过。 https://mp.weixin.qq.com/s/G3xdrI_cqd4RJJvII8CcmQ
- ^文据《全集》历史编卷一校订过。 https://www.23uswx.com/124_124615/46319558.html
- ^《论儒家的发生》,取自《全集》历史编卷三《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68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