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国家在涉及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宣传和历史不分家,立场先行,所以历史学不重视原始档案和文献,同样也根本没有完善的档案解密制度和查阅制度,像你如果要找一个重要会议记录,发现档案没公开,那你这个研究怕是进行不下去了,而且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上就应该允许民间百家争鸣,权威性的结论必然是能引用大量档案说明历史事实,而推翻这个结论往往是新的历史资料被重新发现,像戴维格兰茨作为苏德战争研究的后起之秀,就有很多新的定论,依据的是最新解密的档案。
以苏德战争的历史研究为例,西方和苏联两方的研究经历就可以看出苏式研究方法和西方的区别以及被西方甩开的事实。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15年,是宣传品与回忆录互争雄长的15年。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以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刊行了一大批带有鲜明宣传色彩的出版物“。与之相对应,以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亲身参与东线鏖战的德国军人为代表的另一个群体,则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反击?。这些书籍因为是失败者痛定思痛的作品,著述者本人的军事素养和文笔俱佳,故而产生了远胜过苏联宣传史书的影响力,以至于很多世人竟将之视为信史。直到德国档案资料的不断披露,后人才逐渐意识到,这些名将回忆录因成书年代的特殊性,几乎只能依赖回忆者的主观记忆,而无法与精密的战史资料互相印证。
同时,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些身为楚囚的德军将领大多谋求:一,尽量撇清自己的战争责任;二,推卸战败责任(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败因统统归纳为希特勒的瞎指挥)﹔三,宣传自身价值(难免因之贬低苏联和苏军)。而这几个私心又迎合了美国的需求:一,尽快将西德纳入美国领导的反苏防务体系之中,故而必须让希特勒充分地去当替罪羊,以尽快假释相关军事人才;二,要尽量抹黑苏联和苏军,以治疗当时弥漫在北约体系内的苏联陆军恐惧症;三,通过揭批纳粹政体的危害性,间接突显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此后朱可夫等苏军将领在后斯大林时代刊行的回忆录,一方面固然是苏联内部政治生态变化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说是对前述德系著述的回击。然而,德系回忆录的问题同样存在于苏系回忆录之中。两相对比,虽有互相校正之效,但分歧、疑问更多,几乎可以说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俨然是在讲两场时空悬隔的战争。结果就是,苏德战争的早期成果,因其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而未能形成真正的学术性突破,反而为后人的研究设置了大量障碍。
刚开始的时候差距还不是很大,这个时候德方档案和苏联档案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回忆录和宣传品半斤八两,仅仅可以作为参考。
进入20世纪60年代,虽然各国关于东线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版物汗牛充栋,但摘取桂冠的仍然是当年的当事人一方。幸存的纳粹党要员保罗·卡尔·施密特(Paul Karl Schmidt)化名保罗·卡雷尔( Paul Carell),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德方资料,并对苏联出版物进行了尽量全面的搜集使用,更对德国方面的幸存当事人进行了广泛的口述历史采访,在1964年、1970年相继刊行了德军视角下的重量级东线战史力作——《东进:1941—1943年的苏德战争》和《焦土:1943—1944年的苏德战争》。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趋势开始发生分化。北约方面可以获得的德方档案资料越来越多,苏方亦可通过若干渠道获得相关资料。但是,苏联在公布已方史料时却依然如故,仅对内进行有限度的档案资料公布。换言之,苏联的研究者较之于北约各国的研究者,掌握的史料更为全面。但是,苏联方面却没有产生重量级的作品,已经开始出现军事学说的滞后与体制限制的短板。
结果,在这个十年内,最优秀的苏德战争著作之名被英国军人学者西顿(Albert Seaton)的《苏德战争》摘取°。此时西方阵营的二战研究、德军研究均取得重大突破,在这个整体水涨的背景下,苏德战争研究自然随之船高。而西顿作为英军中公认的苏军及德军研究权威,本身即带有知己知彼的学术优势,同时又大力挖掘了德国方面的档案史料,从而得以对整个苏德战争进行全新的考订与解读。埃里克森为研究苏德战争,还曾专程前往波兰,拜会了苏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个非同凡响的努力成果,就是名动天下的“两条路”。
所谓“两条路”,就是1975年刊行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与1982年刊行的《通往柏林之路》10。正是靠了这两部力作,以及大量苏军研究专著",埃里克森在1988—1996年间成为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主任。
厄尔·齐姆克(1922年12月16日—2007年10月15日)则兼有西顿和埃里克森的身影。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齐姆克虽然在二战中参加的是对日作战,受的也是日语训练,却在冷战期间华丽转型,成为响当当的德军和苏军研究权威。曾在硫磺岛作战中因伤获得紫心勋章的齐姆克,战后先是在天津驻扎,随后复员回国,通过军人权利法案接受高等教育,195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位。1951—1955年,他在哥伦比亚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工作,1955—1967年进入美国陆军军史局成为一名官方历史学家,1967—1977年在佐治亚大学担任全职教授。其所著《柏林战役》《苏维埃压路机》《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东线的抉择》《德军东线北方战区作战报告,1940—1945年》《红军,1918—1941年:从世界革命的先锋到美国的盟友》等书,对苏德战争、德军研究和苏军研究均做出了里程碑般的贡献,与埃里克森堪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战史研究可以说是被西方全方位吊打,我们熟悉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通往柏林之路》、《东进》、《焦土》等苏德战争的经典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注意西方研究仅仅靠苏联公开资料和宣传资料和德方解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苏联这边既可以去查到德方档案,又有自己的档案,学者本来可以做出有成果的研究,但是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别急,后面会说。
等到苏联解体之后,档案公布,又有一大批学者利用苏联档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戴维格兰茨就是这个时候崛起的,解密的苏联档案可以说是把苏联老底揭了个底朝天,之前苏联出版的官方战史基本可以用科幻作品来概括,斯大林瞎指挥、苏军各种神话的破灭、督战队,最新2020年俄罗斯公布的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就有1200多万,可以说就是一场用人堆出来的胜利。所以为啥苏联的战史研究落后,又回到开头说的,宣传和历史不分家,就需要历史怎么有利于宣传怎么来,事实不重要,立场最重要。像有些档案为啥不公布呢?很简单,就是事实恐怕真的不好看,所以不公布
沈志华等一众历史研究者为什么在一些人风评不好,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试图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用档案和文献说话而不是依据官方的宣传口径来研究,这就必然对现有的体系造成冲击,并且得出很多“大逆不道”的结论。这必然是一些人接受不了的。
另外国内很多历史研究缺了完整的注释和档案来源这一环节,随便找几个人的书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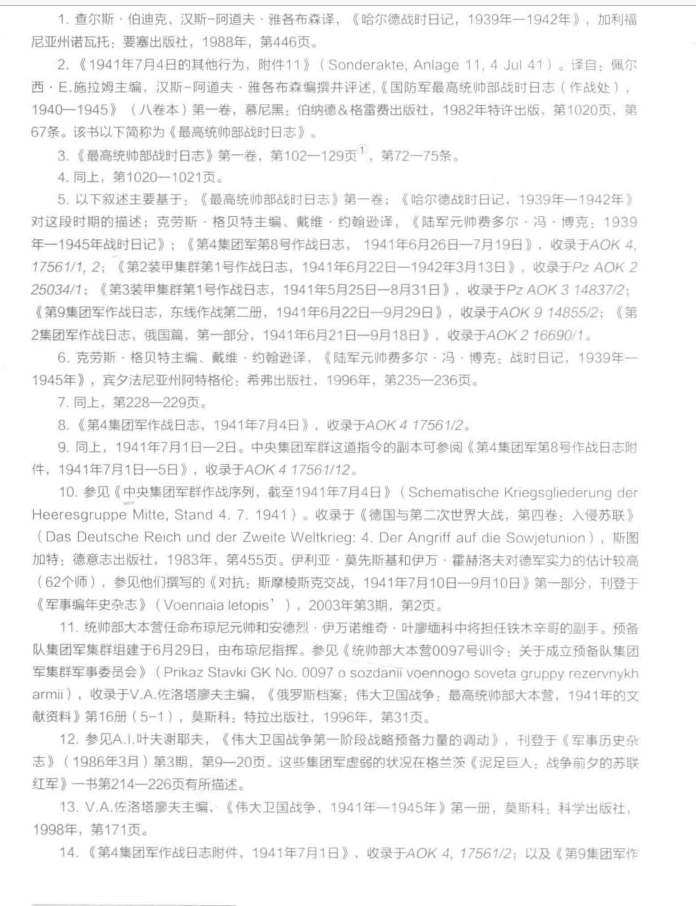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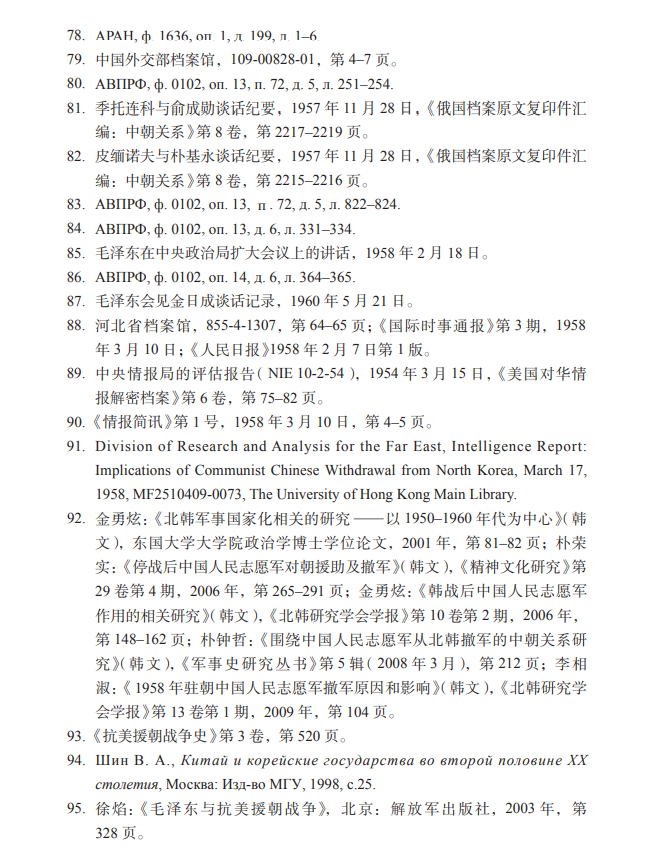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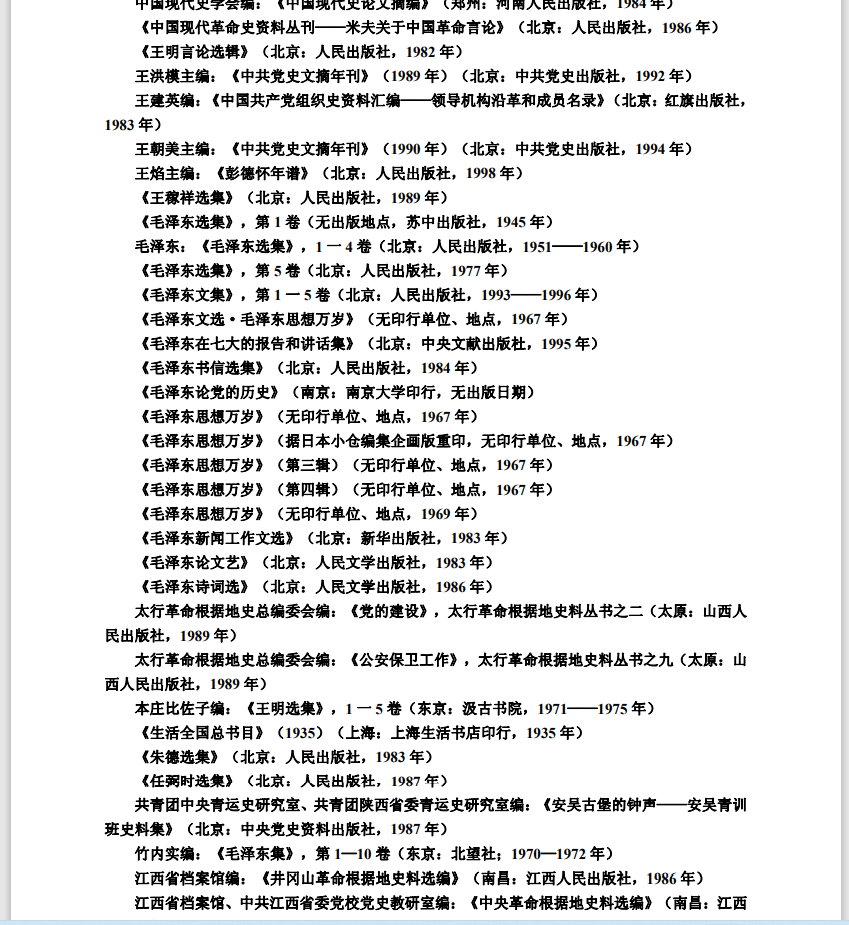
我还想起北风大佬,这位也是用档案论证了当年在陕北卖特货的历史,当时评论区有人说是黄金,北风直接把档案拿出来,内部文件甚至连“特货”都不用,直呼其名。那个人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非常好笑。
其实看不惯沈志华也不是没有办法反驳他,你也可以查查原始档案,看看能得出啥结论,自己写篇文章指出错误,还可以向国家档案馆申请公开档案来打沈志华的脸,我是强烈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