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刚刚在驳斥台湾方面(主要是帅化民)抱怨大陆把国军正面战场“隐形”论调,严肃批判过这个事儿,沈大炮当时眼睛都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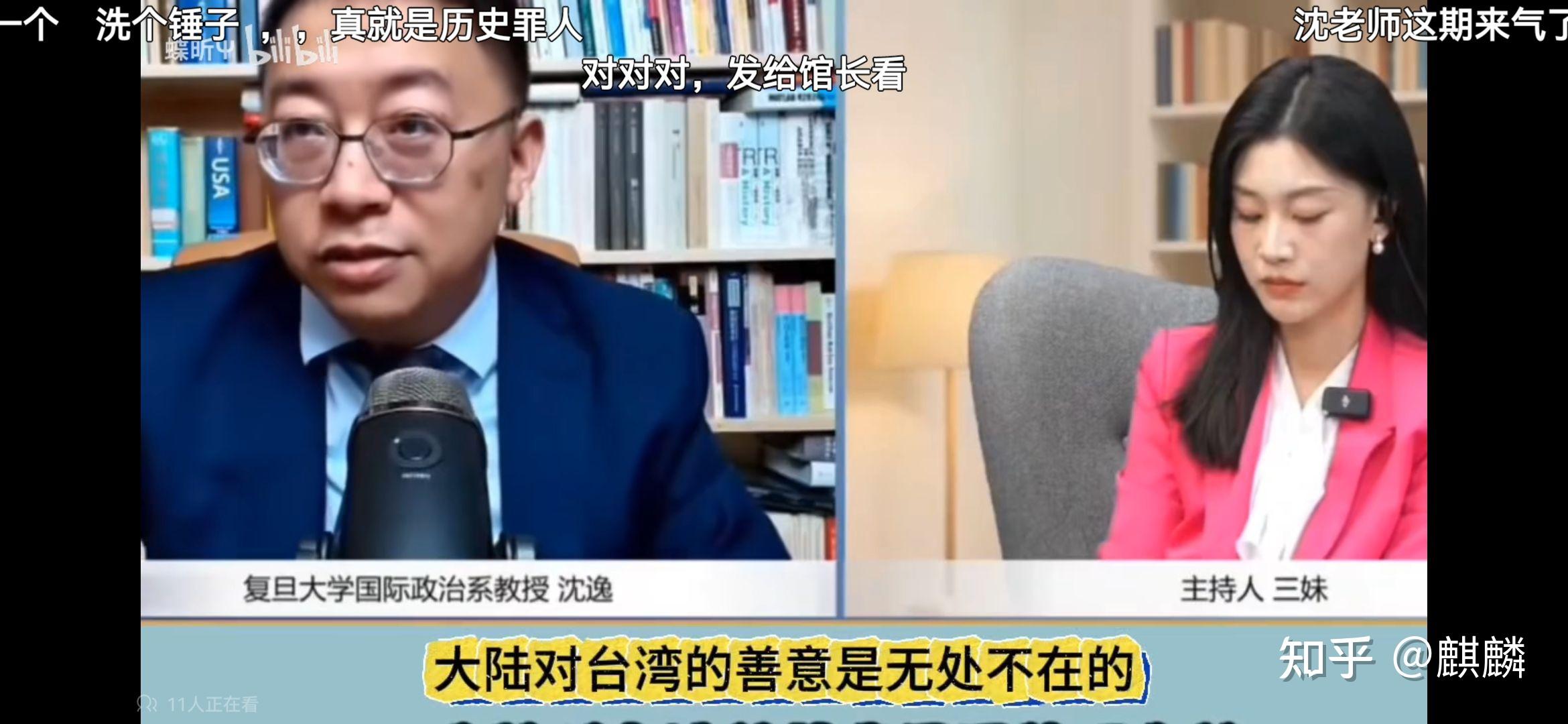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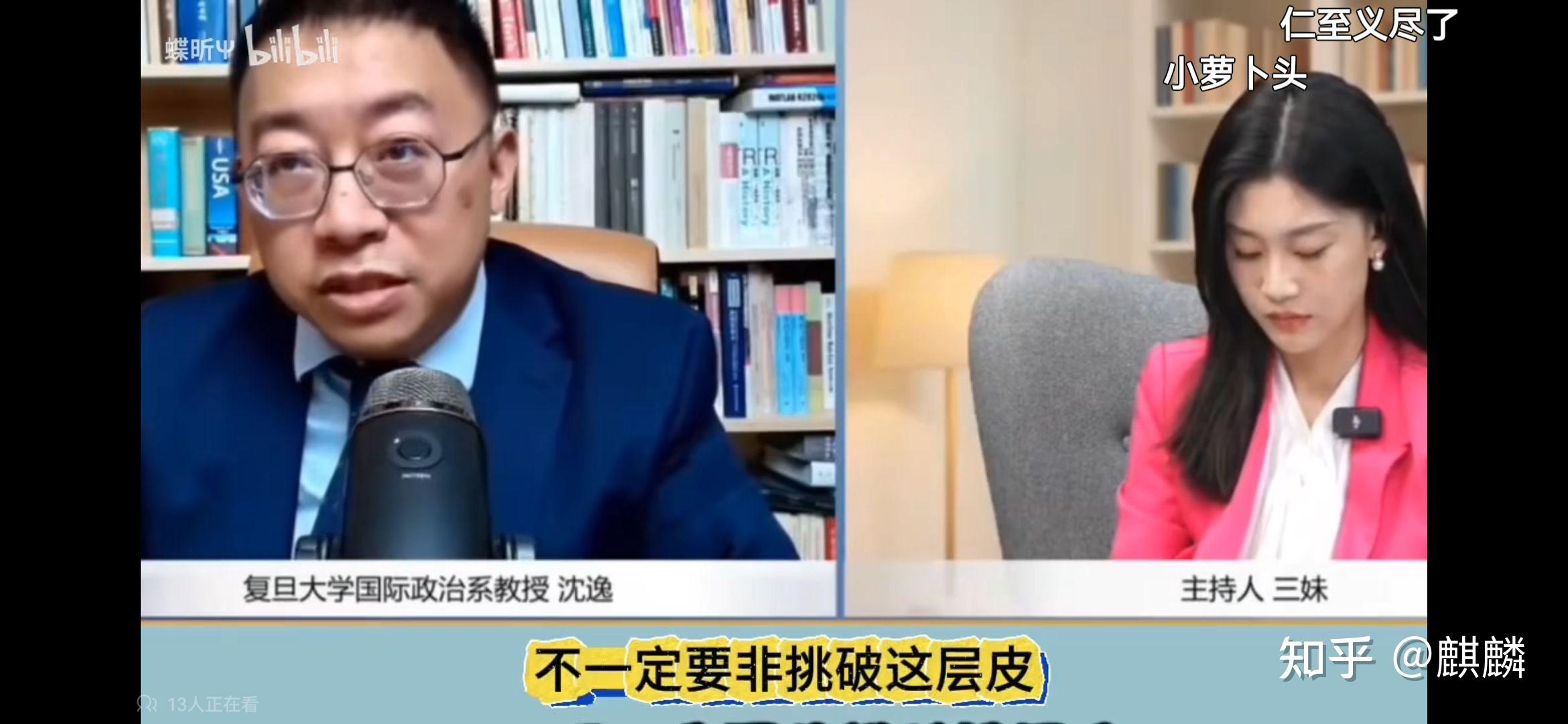

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根子上就是老蒋要打“国际观瞻”,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根本目的根本不是守住,而是吸引国际注意力,引起国际主要国家干预。
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为了“国际观瞻”(即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干预)而做出的决策,导致了许多从纯军事角度看本可避免的惨重损失。这些决策的初衷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但其军事代价极其高昂。
在敌绝对海空炮火优势下,选择在淞沪三角地带决战。这是最根本也是代价最大的决策。
上海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几乎没有天然屏障。中国军队完全暴露在日军舰炮(来自长江上的舰队)和航母舰载机的猛烈火力之下。
从军事角度看,在这样一块无险可守、且敌方海空力量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区域与敌进行主力决战,是极其不利的。理想的策略应是诱敌深入,利用中国广阔的国土和复杂的地形(如山地)抵消日军的装备优势。
蒋介石和政府决策层认为,必须在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各国利益交汇之地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才能“打给外国人看”。他们希望西方列强看到日军的残暴和中国的英勇,从而出面调停甚至干涉。这个政治目标压倒了军事上的合理性。
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寸土不让”的决心,蒋介石和最高指挥部多次下令部队死守无法长期坚守的阵地,甚至反复争夺已化为废墟的据点。
奉命“死守宝山”的第98师583团3营500余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与拥有绝对炮火和坦克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日,最终全营壮烈殉国。从战术上看,这座孤城并无死守到底的价值,但其象征意义和对外宣传的价值巨大。
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罗店争夺战”,双方反复拉锯,中国军队整营整团地填进去,损失了数万精锐部队,因此被称为“血肉磨坊”。虽然罗店具有一定的战术重要性,但如此不计代价的消耗战,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展现决死的态度。
1937年11月初,中国军队已苦战近三个月,伤亡惨重,筋疲力尽,战线已难以维持。此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11月3日开幕)。蒋介石希望军队能在上海再坚持一下,以便在会议上争取更有利的国际支持。
最高指挥部因此迟迟不下达撤退命令。当11月5日日军第10军突然在金山卫大规模登陆,企图包抄中国军队后方时,前线部队已因拖延而陷入极度疲惫,调整部署为时已晚。
等到11月8日晚终于下令全面撤退时,命令仓促,组织混乱。各部队拥挤在有限的几条公路上,遭到日军飞机昼夜不停的轰炸扫射,秩序荡然无存,撤退变成了大溃败。许多精锐部队在此过程中被打散,重装备损失殆尽。原本有序的撤退本可以保存更多有生力量,但为了等待一个渺茫的国际干预希望,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在战役初期就打出气势,国民政府将其倾国力打造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化精锐部队(如第87师、88师、36师等德械师)最早投入战场。这些部队在上海市区的巷战中虽然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但自身也遭受了巨大伤亡。这些宝贵的战略预备队本应用在更关键的战役转折点,但为了追求初期的“国际观瞻”效果而被过早消耗。
守南京也是一样,最终目的还是象征性的打一下,可怜十万大军在统战部眼里只是配合作戏的演员而已。
南京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延续了淞沪会战的逻辑,即“国际观瞻”和政略考量严重影响了军事决策,并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两者一脉相承,南京保卫战可以说是淞沪会战决策失误的延续和升级。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它的存弃关乎国家尊严和国际形象。从政治和情感上讲,轻易放弃首都是难以接受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希望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以向国内外展示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
从纯军事角度看,死守南京是一场必败之战。参战部队多是刚从淞沪战场溃退下来的残部,损失惨重,未得休整,人员和装备都远未恢复。
南京背靠长江,日军可以完成北、东、南三面的陆上包围,并用海军封锁西面的长江。中国守军一旦被围,退路极易被切断,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虽然外围有紫金山、雨花台等高地,但环城线过长,以当时可用的兵力根本无法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
在高级军事会议上,绝大多数将领(如李宗仁、白崇禧、陈诚等)都认为象征性地稍作抵抗后应主动撤退,保存有生力量。但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主动请缨担任城防司令)的意见,决定进行短期固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国际观瞻”,等待《九国公约》国家可能的干预。
淞沪会战是“打给外国人看”,而南京保卫战则直接牵扯到了在南京的外国人。
战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如约翰·拉贝等)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划定了难民安全区。
国民政府对此给予了支持,并承诺军队不会进入安全区。这一举措本身带有强烈的国际宣传色彩,希望借助第三方力量保护平民,并向世界展示日军的暴行(后来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守城部署,并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国际社会的存在或许能对日军形成某种制约(事实上日军基本无视了安全区)。
蒋在撤离南京前,一方面要求唐生智“固守”,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指示“相机撤退”,命令模糊,让唐生智无所适从。
在守城战进行到最危急关头(12月12日),唐生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仓促下令撤退。但他先前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已下令各部销毁了大部分渡江船只,并要求官兵“与阵地共存亡”。这个突然的撤退命令与先前的死守要求完全矛盾。
命令下达后, communication 系统失灵,很多部队并未接到命令。接到命令的部队涌向下关码头,却发现船只寥寥无几。官兵们纷纷自制木筏渡江,或在混乱中丢弃武器、脱下军装逃跑。组织完全崩溃。
结果,大量中国军人未能渡江,被困在南京城内。这些失去抵抗能力的溃兵和平民,成为了随后进城日军进行大规模屠杀(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对象。可以说,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直接加剧了后续人道主义灾难的规模。
与淞沪会战相比,南京保卫战的决策更加脱离军事现实。淞沪会战至少达成了战略上的部分目标(如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而南京保卫战在军事上几乎毫无益处:
未能有效消耗日军:守城时间短(约一周多),未能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未能成功撤退:最精锐的教导总队等部队在溃退中损失殆尽,大量有生力量被无谓地消耗和俘虏。
混乱的撤退直接导致了南京守军和平民的巨大灾难,为日军实施大屠杀创造了条件。
因此,南京保卫战是淞沪会战“政治优先于军事”思维的更为极端的悲剧性延续。 它深刻揭示了一个弱国在面临强敌时,若不能清醒地在“政治象征”与“军事存续”之间做出权衡,仅仅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将会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