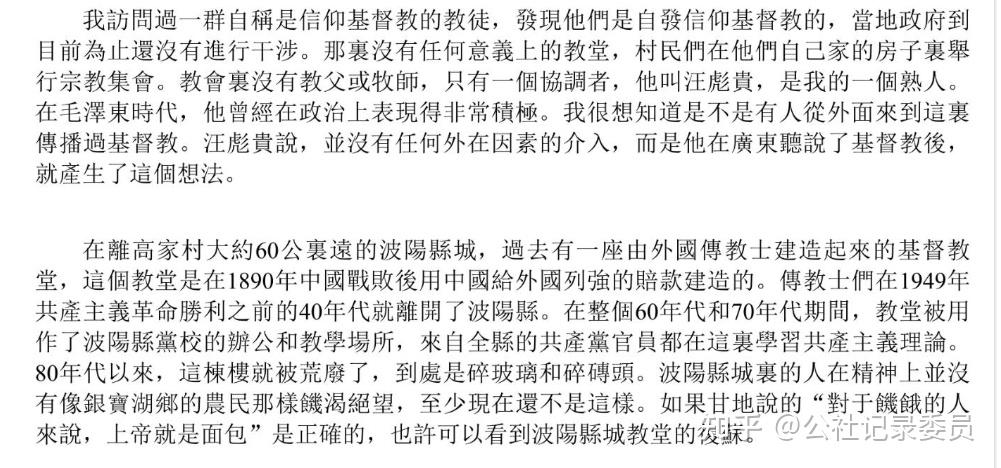话说回来,其实,高默波老爷子的论述里最初的八十年代宗教复辟浪潮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因素。农村医疗系统作为毛子任的遗产被废除后,“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系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總的來說,1949年以來,農村醫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進的醫療技術,如疫苗接種,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兒童的死亡率。衛生教育也幫助高家村人預防了許多以前困擾他們的常見病,政府的各種措施控制了致命的“血吸蟲病”瘟疫。在毛澤東時期,醫療改善最顯著的特徵是,那些最貧困和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優待。然而,80年代以來的改革政策無視那些最沒有地位的人。盡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腳警生”體制似乎對高家村人來說還算運作得比較好。現在,這種體制已被抛棄了。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系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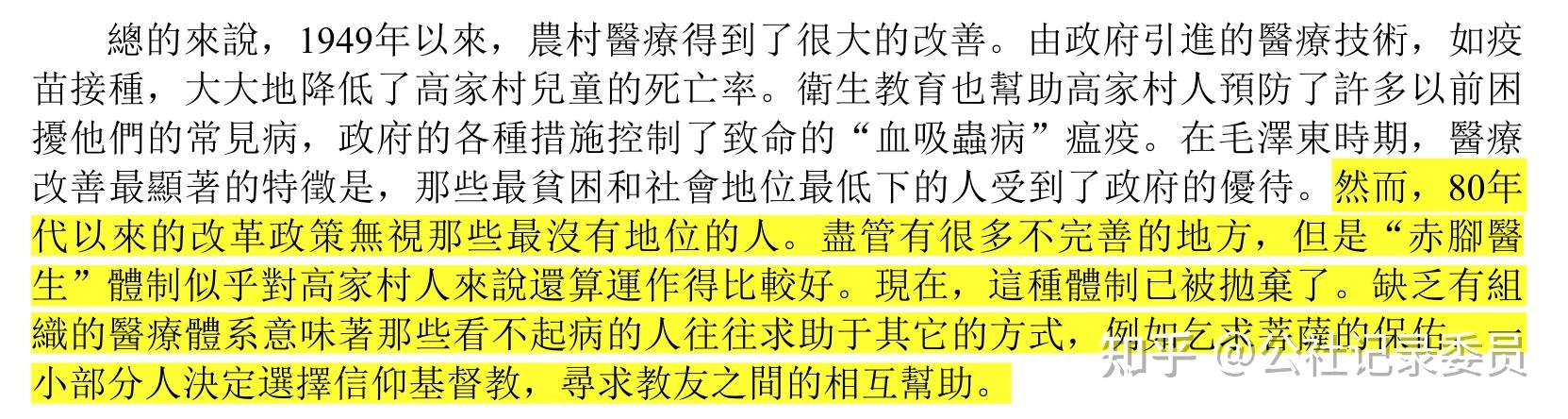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上层建筑变动导致医疗政策变迁,又反作用到基层的医患矛盾上
……1980年以來,縣政府還沒為農民做過什么事,用來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的所有地區防疫站都被拆除了,縣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並且嚴重缺乏資金。1992年,當我重返我以前接受過血吸蟲病治療的醫院時,幾乎看不到病人,這個地方看上去像被遺棄了一樣。因為現在不再是免費治療血吸蟲病,只有少數人才能承擔得起在醫院治療的費用。因此,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驚訝。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蟲病。鄉裏的診所給他們開了藥叫他們自己回家服用,並且每個療程花費了20多元錢。當地政府對瘟疫再現的危險早有預料。1994年,我就在江家村的牆上看到了一行大字標語,寫著“再送瘟神”,這裏套用的是1958年毛澤東寫的那首詩《送瘟神》。
因為母親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當時,那裏有一位醫生正在為村民們巡回檢查血吸蟲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我催促他們盡早治療。然而,他們的回答使我大吃一驚。他們想到波陽縣醫院再去檢查一遍,因為他們不相信當地的醫生。他們說,那個醫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們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好讓他們到他那兒去買藥。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確患有這種病,還是醫生故意錯診,這都意味著要么血吸蟲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醫生確實是出于個人謀利的考慮而有意錯診。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什么好的跡象。
1981年,“赤腳醫生”合作醫療體系被廢除。原來大隊的三個醫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診所。同時,村民們越來越不願意去看病,因為他們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錢,並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錢。按照當地的生活水準,這三個醫生都變得非常富裕。高時華在80年代又建了一棟房子,這次是用磚頭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後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個遺孀和三個孩子。江醫生建了一棟有十個房間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後院有個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個汽車停車場,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單獨的廚房。江醫生是這個地區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徐醫生也建了一棟像城堡的房子,大廚房裹還挖了一口井。這口井裝有一個電動水泵,只要一按按鈕,水就會自動出來。徐醫生家是青林地區唯一採用電動水泵抽水的人家,這種方式比用壓水機壓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給了別人,村民們還不斷地把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送給他,作為對他的醫療服務的回報。他曾經吹噓說,別人給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讓他的家人只好拿來喂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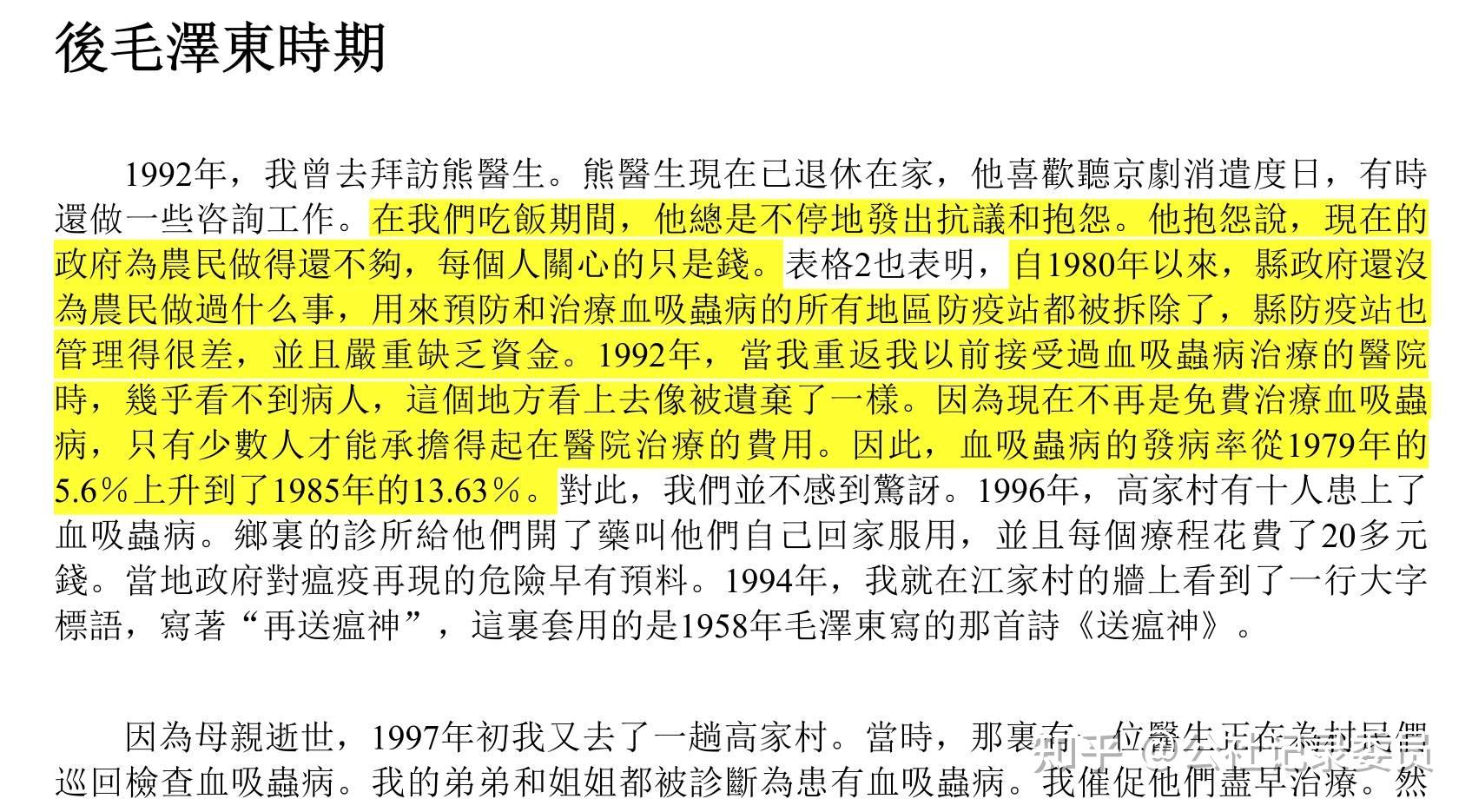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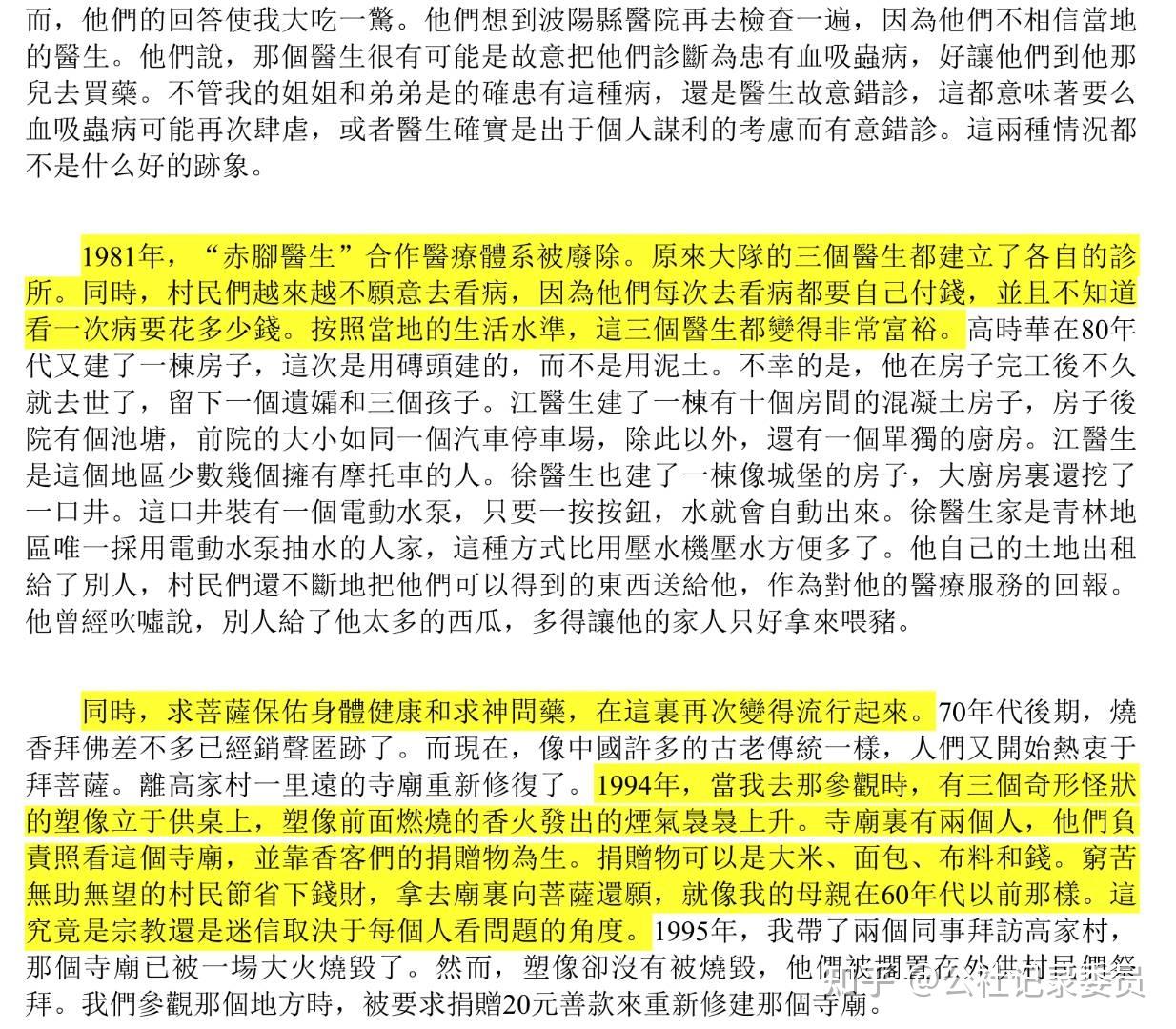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复兴开始重新出现,
同時,求菩薩保佑身體健康和求神問藥,在這裏再次變得流行起來。70年代後期,燒香拜佛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而現在,像中國許多的古老傳統一樣,人們又開始熱衷于拜菩薩。離高家村一里遠的寺廟重新修復了。1994年,當我去那參觀時,有三個奇形怪狀的塑像立于供桌上,塑像前面燃燒的香火發出的煙氣裊裊上升。寺廟裏有兩個人,他們負責照看這個寺廟,並靠香客們的捐贈物為生。捐贈物可以是大米、面包、布料和錢。窮苦無助無望的村民節省下錢財,拿去廟裏向菩薩還願,就像我的母親在60年代以前那樣。這究竟是宗教還是迷信取決于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1995年,我帶了兩個同事拜訪高家村,那個寺廟已被一場大火燒毀了。然而,塑像卻沒有被燒毀,他們被擱置在外供村民們祭拜。我們參觀那個地方時,被要求捐贈20元善款來重新修建那個寺廟。
在這個地區,我還發現有基督徒。對此,我也感到很驚訝。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這裏沒有一位記錄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後到80年代後期,也不可能有人在這個地區傳教。在我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現在據說在這個地區將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們大約一個月聚一次;在農閒季節,他們聚得更頻繁。他們用漢語唱基督贊歌,並向基督耶穌祈禱。1992年,當我在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鄰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裏拜訪他們時,我看到在聖壇後面的牆上用大筆畫書寫著的中國漢字“愛”,每一個筆畫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義的很小的一些漢字組成,包括“愛是恒久忍耐”,“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只喜歡真理”,“不計算人的惡”,“不求自己的益處”,“不作害羞的事”。聖壇上擺放著兩個熱水瓶,一個大茶缸,兩本中文版的《聖經》,還有一本基督教雜誌《天風》,封面上畫著聖母瑪麗亞、聖嬰基督和一群天使。
現在住在高家村的村民還沒有一個是真的基督徒。我遇到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婦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現在住在江家村。我問她是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說,那些人很善良,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互相幫助。在困難時期,比如生病和欠債的時候,他們會互相幫助,像到地裹幫別人干活,互相借錢和其它的東西。至于他們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很顯然,由于沒有政府機構的支持,他們形成了一個合作團體來互相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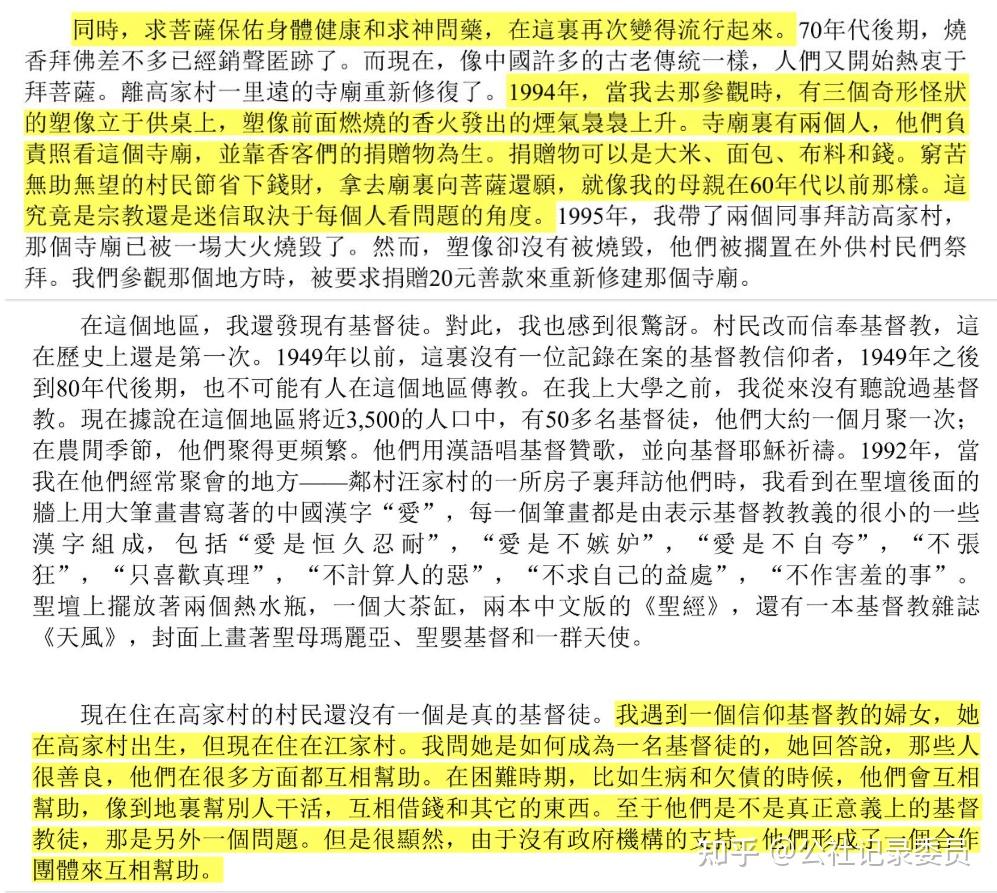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论述里往昔的基层组织崩溃,然后才出现宗教复辟,二者处在对立状态。但是,在高默波先生的阐释中指出部分宗教的组织人士就是毛子任时期的积极分子。
我訪問過一群自稱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發現他們是自發信仰基督教的,當地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干涉。那裏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教堂,村民們在他們自己家的房子裏舉行宗教集會。教會裏沒有教父或牧師,只有一個協調者,他叫汪彪貴,是我的一個熟人。在毛澤東時代,他曾經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積極。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從外面來到這裹傳播過基督教。汪彪貴說,並沒有任何外在因素的介入,而是他在廣東聽說了基督教後,就產生了這個想法。
在離高家村大約60公裏遠的波陽縣城,過去有一座由外國傳教士建造起來的基督教堂,這個教堂是在1890年中國戰敗後用中國給外國列強的賠款建造的。傳教士們在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之前的40年代就離開了波陽縣。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教堂被用作了波陽縣黨校的辦公和教學場所,來自全縣的共產黨官員都在這裏學習共產主義理論。80年代以來,這棟樓就被荒廢了,到處是碎玻璃和碎磚頭。波陽縣城裏的人在精神上並沒有像銀寶湖鄉的農民那樣饑渴絕望,至少現在還不是這樣。如果甘地說的“對于饑餓的人來說,上帝就是面包”是正確的,也許可以看到波陽縣城教堂的復蘇。